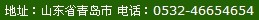|
上元节。 皇觉寺为了迎接圣上的到来,提前好几天便开始清路,禁止百姓出入。 寺院里的散客流民们也得了禁止出入的告诫,以免冲撞了皇上。 宁遥平日里人缘好,又常常在寺院里帮忙,找相熟的法师借了身祖衣穿了,谎称想一睹天颜,法师见她说得诚恳,又耐不住她痴缠,竟真同意了。 她混在迎接队伍的最尾端,瞧着硕武帝浩浩荡荡地踏过山门,身后跟了一长串的太监侍从。到了皇觉寺,便由几个方丈和主持接引着在寺内跪拜焚香,祈福祷告。 礼毕后,日头已经到头顶了。硕武帝在寺里用过斋饭,便由僧人领着进了去了寺庙东边的净室。 皇觉寺东边有六七间净室,殷绥就其中一间净室里诵经。他刻意不把门关实,留了条门缝出来,被冬日里的寒风一吹便吱吖作响。 硕武帝瞧见那扇半开着的门,又听见里头似有若无的念经声,眉心一动,下意识往里头瞧去,却只瞧见一个被笼在模模糊糊的侧影。 硕武帝问:「那人瞧着也不是寺院里的僧人,怎么这会子寺院里还有旁人?」 了缘法师忙站出来,双手作揖鞠了一躬。 「阿弥陀佛,这是我们这儿的一个香客,许是没通知到他,贫僧这就带他下去。」 门被完全推开。 殷绥坐在靠窗的案几前,坐姿端正,气度矜贵,手里还捧着卷未抄完的佛经。听见开门的声音,他也不做声,只是慌忙站了起来低着头行了个礼,便抱起案上的几卷佛经急张拘诸地往外走。 走到门口时还不小心绊到了门槛,手里的佛经散了一地。 鲜红色的字体大刺刺地映入眼帘。 是《无量寿经》和《金刚经》。 字体苍劲有力,结构严整,一看便是下过重功夫的。 硕武帝瞧见眼,忍不住叹了句:「施主有心了。」 殷绥依旧微低着头,也不回话,随意点了点头,飞快地拾着地上的佛经。 「皇上同你说话呢!」硕武帝身旁随行的公公道。 殷绥这才压着声音应了声:「算不上用心,为人子女应尽的本分罢了。」 他故意压低了几分,可少年的声音依旧清凌凌的,极具辨识度。 硕武帝闻言,心下有些怪异,道:「你抬起头来。」 殷绥依言缓缓抬起头来,如玉的脸上瞧不出半分情绪,可眼尾却微微泛着红。 硕武帝瞧了他半晌,微微蹙眉:「你是......绥儿?」 「草民不懂皇上在说什么,许是圣上认错人了罢。」 殷绥答道,只是这红了又红的眼尾实在没有什么说服力。 他生得实在像极了他母妃,容貌昳丽。 一双微微上挑的丹凤眼,不笑时便似鹰隼,目光锐利。可若是一笑便含上了水光时,顾盼流转皆是情意。 硕武帝瞧着心口一疼。 他想到那人离开时也是这般地瞧着他,面容沉静,也不言语,就拿一双浸着水光的眼定定地看着他。 她那时已经病了,身形瘦弱,病歪歪地躺在床上。明明衣着素净不施粉黛,面容也是雪色的苍白,却更显出一股羸弱消瘦的美来。 让人闻之往俗,见之不忘。 终究还是他有愧于他们母子。他愧于靖柔,也愧与他。 他是他的孩子,千尊万贵的皇子,却在九岁就被送往椋城,由皇后的人照顾着,一直没什么消息传来宫里。 他也繁忙,鲜少过问。 这孩子本来也没做错什么,是因着他才背上了「不详」的名声,无辜被牵。 他还记得他离宫时的样子,小小一个,虽性子淡漠不喜言谈,可见着他时,总是乖巧和顺的。 这孩子曾是他的骄傲。 他是他最喜欢的女人的孩子,又生性聪慧,曾得过太傅的夸赞,说他是天纵之才,只是可惜...... 只是可惜,他是江家的孩子,靖柔她......本不该有孩子,就算有,也不应该是皇子。 好在现在江家已经没有了。 半晌,硕武帝缓缓叹了口气。 「绥儿,你......可是在怪朕?」 殷绥忙跪下身去:「儿臣不敢。儿臣只是......」 「儿臣乃不祥之人,奉父皇诏令前往椋城,本就不该出现在父皇面前。」 「奈何儿臣实在思念父皇,这才一个人偷偷跑回上京。」 「儿臣原来只想趁着上元佳节,偷偷瞧上父皇一眼,未曾想还是冲撞了父皇,还请父皇责罚。」 他说罢,俯身恭恭敬敬磕了个头。 硕武帝闻之又是一声叹息:「你什么时候来的?路上吃了不少苦吧?」 殷绥沉默了会儿,垂眼道:「儿臣想趁着上元节见父皇一面,这两天才到这儿。」 硕武帝微微颔首,又瞧了眼他手里的佛经——这么多的血经,样样工整,没个十天半个月是抄不完的。 「那这是怎么回事?」 硕武帝问。 了缘法师犹豫了会儿,站了出来。 「阿弥陀佛,施主,佛寺之内万万不可诳语。」 「这位施主自年二十九日便到了寺中,这半个月来,一直在佛堂内修心打坐,誊抄佛经。」 「施主诚心,曾向贫僧请教了用血誊抄佛经的要点,日日茹素念佛,断盐少油。以恭敬心发愿,以祈家人平乐安康。」 硕武帝闻言,拿过殷绥手上的经书,细细瞧了瞧。 「也难为你诚心。」 殷绥这才抬起眼来:「儿臣罪己之身,无福在父皇母后身旁尽孝,只能每日诵经百遍,以身供养,只愿父皇额娘岁岁欢愉,愿这天下平安顺遂。」 宁遥躲在净室后的竹篱里,透过窗外往里瞧。 这一瞧就瞧见—— 殷绥微仰着面微笑,双眼微红,睫毛轻颤,眼里的泪要掉不掉的含在眼眶里,隔了好一会儿才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一颗颗滚下来。 好家伙,瞧着她的心都开始疼了。 这演技,这颜值……可惜生错了时代,不然全世界都欠他一座小金人。 什么叫琼瑶式哭戏,她可算是见到了。 宁遥感叹了一声,当未来的BOSS太不容易了。 不仅要能伸能屈肯吃苦,还要能哭会道能绿茶。 不容易啊。 与皇上会面后,钮祜禄·绿茶·绥凭借自己精湛的演技和献身精神,当天下午便顺顺利利回了宫。 不仅回了宫,硕武帝为了避免他「不详离宫」这一段过往为人诟病,特意给他改了玉碟,把原生辰推后了两日,对外只说是他说因为紫微星不稳,所以才外出祈福,祈愿天象稳定,再不肯人提「不详」这两个字。 对比,宁遥感慨万千,殷绥则是满心的讥讽。 ——如果不是江家倒了,他就算再心疼他,也断然不敢这般。 当然,即便是再讽刺,他也只是微垂下头,任由长而翘的羽睫覆盖下来,面上乖巧又感激。 殷绥回宫的时候,宁遥就躲在后山的树丛里静静看着他,直到人影慢慢消失、变成了远方一个模模糊糊的小点儿,她才抬起头来看向天空,呼出一口长长的白气儿。 很快……他们也要回宫了。 她看了这么多年宫斗连续剧,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居然能真的踏进皇宫里。 果然人生总是这样,充满了未知和意外。 宁遥和全顺回宫的那天,天空中飘着绵腻的细雨。 长廊,高墙,四方天。 他们一进宫,就被人领着到了皇后的朝阳宫。 这个系统口中面慈心狠、手段毒辣的女人正端坐在椅子上,微垂着眼,手里不断转着佛珠。 「回来了?」 她穿戴素雅,可姿态却是雍容而华贵的,声音低沉,透着沉重的怠倦。 宁遥和全顺慌忙跪下,异口同声:「请娘娘恕罪!」 「是奴婢奴才办事不力,没有看住九皇子,让他趁机偷偷溜了出来。」 「两个废物!」 皇后总算抬起眼来,瞧了两人一眼,把手里的佛珠重重往案前一放,又把目光定在宁遥身上。 「紫芙,你是我一手教出来的人,虽比不得丹栗等人,但也算是我的心腹,我对你一向是寄予厚望的。」 宁遥把头埋得更低。 「你可知道背叛本宫是什么下场?」 「紫芙不敢……」 「不敢?」皇后冷哼一声,手指因为用力而透出青白的骨节来。 「你若是不敢,殷绥他又怎么能回宫?」 「我让你「好好照顾」他,可如今呢?」 皇后说着,把佛珠猛地一掷,砸在宁遥的头上。 霎时间鲜血直流。 宁遥却管不上这些,她甚至连痛也没察觉到,只是一个劲儿地磕头。 毕竟她不清楚殷绥会不会真的保他,更不清楚他什么时候会来。 她只能先保住她自己。 「奴婢冤枉!还请娘娘明察!」 「奴婢虽然蠢笨,可对娘娘一片赤诚,绝无二心!奴婢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娘娘……还请娘娘明鉴!」 话音还未落下,宁遥就听见身后有脚步声从远到近,接着一双如玉的手出现在她的视线里。 殷绥缓缓拾着地上的佛珠,脸上还带着丝乖顺的笑意。 他先是深深看了宁遥一眼,这才轻笑着给皇后行礼问安。 「母后今日好大的火气,连平日里常常供奉的佛珠都砸了。」 「左不过是两个奴才罢了,若是气坏了身子可就不值当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皇后面色一变,也露了个温婉慈爱的笑来,瞧着倒是一片母慈子孝。 「你倒是有孝心,日日过来请安。」 她说罢,又转头对外头的人厉声道,「怎么小九过来都没人通报本宫一声吗?」 话音未落,殿内的珠帘被人缓缓掀起,一穿着团龙纹便服的人走了进来。 「是朕不让他们通报的,没成想倒是瞧见这一幕。」 皇后微微一愣,脸色有一瞬间的僵硬。 「陛下怎么来了?」 硕武帝笑了,一贯严厉的脸上难得多了几分赞许和温情。 「朕今日和小九下棋,许了他个彩头。结果他竟要到你这儿来了。」 殷绥也笑道:「既然这两人犯得不是什么大错,那儿臣就斗胆讨这个赏了。」 「儿臣刚从宫外回来不久,还不大习惯,身边也没个得心应手的人。」 「倒是娘娘身边的紫芙,被娘娘管教得甚好,在椋城时就侍奉在儿臣身侧,事事为儿臣考虑。」 「之前儿臣重病,若不是她发现的早,每日侍奉汤药,儿臣怕早就无缘在父皇母后身边进孝了。」 「这几年下来,儿臣也早就习惯了有她侍奉,换了旁人反倒是不太如意。所以才斗胆借着父皇的彩头,向母后求人。」 「母后向来仁爱宽厚,又疼惜儿臣,一个犯了错的下人罢了,不如待儿臣回了景福宫,再替母后好好责罚她。」 皇后的面色越来越沉,却碍着硕武帝在场,无可奈何地继续起这场母慈子孝的表演来。 宁遥默默啧了声。 果然,要对付白莲,还是得绿茶。 宁遥和绿茶绥离开以后,皇后气得摔了个茶盏。 上好的景泰蓝碎裂开来,泛着冷光。 她睨着依旧跪在地上的全顺,冷笑一声。 「既然那小子把紫芙要走了留下了你,那你就好好说说你知道的事,若是说不好……」 全顺整个人都在抖。 他跪得腿脚发麻,听了这话,忙不迭忍着痛爬到皇后身旁,连手心被碎片划伤都不觉。 「娘娘……奴才的确有事情要告诉您……」 景福宫是皇宫东面、给皇子的住所里最僻静的一间。 这儿原是给病弱的三皇子养病用,后来三皇子故了,宫殿也空了出来,直到殷绥母妃故去后,才简单收拾了一番,让殷绥住了进去。 这次殷绥回宫,皇后为了表示对他的挂念,特意命人把宫殿修缮了一番,可虽说是修缮,除了几个主要住人的地方,其他地方一推开门,依旧能闻到一股隐隐的霉味,到了晚上,甚至还能听到吱吱的老鼠声。 宁遥回去这一路上都很忐忑,殷绥也不知道跟谁较劲似的,一路越走越快。 好容易到了景福宫,她还没来得及松上口气儿,殷绥便把她拽紧了偏厅内,又让原本在里头打扫的人退了下去。 他过头来瞧她脸上的新结好的血痂,微微皱眉:「姐姐受苦了。」 「过来我给姐姐擦一擦。」 宁遥摸了摸自己的额头,讪讪一笑。 她方才是怕极了的。 她自幼胆小,更是怕苦又怕疼。被猛地砸了这一下,疼得不行,偏偏形势又比人强,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现在好容易放松了些,反而察觉到疼了。 她轻轻嘶了声,身子却往后一退下,避开了殷绥的手。 殷绥神情一凝。 宁遥轻轻叹了口气。 「殿下,我们现在回宫了。 「在宫里,你是主子,我是侍奉你的宫女,可千万不能再……」 她想说可千万不能再像前些日子在椋城一样,可殷绥却先她一步打断她。 「之前在椋城姐姐不也是这样对我的吗?」 「姐姐也有替阿绥上药不是吗?」 「更何况……」他自嘲一笑,薄而艳的唇微微掀起:「我又算是个什么主子?」 「姐姐瞧瞧这宫殿,老旧,偏远,是所有皇子住所里最偏僻的那一间,若不是我住着,连定期打扫的宫人也不会有。」 「皇后说这儿僻静,我身子不太好,适合静养。母妃去世后,我便一直住在这里,现在虽回了宫,也还是住在这里。」 「我虽是回来了,可既无父皇宠爱,又无母妃庇佑,还有一堆人躲在暗地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悄悄亮出刀刃来捅上一刀……」 「我身边只有姐姐这一个可信可用之人了。还是说……姐姐回了宫便不想和阿绥一道了?」 他说话时微垂着眼,睫毛微颤,眼角微红。 自下而上瞧着宁遥时,双眼还微微浸着水光,像极了某种小动物。 宁遥再硬的心也给他瞧软了。 真是,惯会装可怜的。 可她偏偏就吃这一套。 她在心底吐槽了句,又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放柔了声音。 「算了,反正现在也没人,之后有人的时候可不能这样了。」 殷绥笑了,这一笑便有星光从那双漆黑的眼里慢慢渗出来。 「阿绥自然会注意的。」 宁遥应了声,想了想又道:「阿绥,你刚刚……为什么要对皇后说那些话?」 「哪些?」他偏头,脸上一片稚气,乖巧又无辜,仿佛真的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 她微微一怔,好看的远山眉打起了结。 殷绥仍旧在笑着,可笑意却未达眼底。 「阿绥说的都是实话不是吗?」 「姐姐不让阿绥说,难不成……姐姐,还有其它的打算?」 宁遥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我能有什么打算?还不是担心你……」 「不管怎么样我都曾经是皇后的人,你这样气她,能有什么好处?」 「更何况……如果她能信我,你把我放在她身边,会比放在你身边要有用得多。」 殷绥似是没想到她会这样回答,微微一顿,很快又弯起眼来,脸上的笑也多了些真心实意。 「姐姐对阿绥好,阿绥自然也会对姐姐好。」 「把姐姐一个人丢在狼窝了,阿绥舍不得。」 这边宁遥安安心心在景福宫里住下了,而那边…… 殷绥回宫不过三日,皇后娘娘就生了场大病——先是在祭祖时无缘无故晕厥,醒来后更是愈发严重,连着痛了好些日子。 朝中大臣在议论纷纷,都说皇后在祭祖时晕倒可不是吉兆,定然是宫中有大变故,冲撞了先祖,这才降下警示来。 又有大臣把矛头指向了殷绥,说他本就不详,这次回宫更是冲撞了先祖和皇后,若再不采取措施,怕是要惹来天怨。 「你不觉得皇后这病来的蹊跷吗?」殷绥问。 宁遥点头,满脑子都是—— 「剪秋,哀家的头好痛啊……」 果然不管在哪儿,头风都是个好东西,想痛就能痛,还不需要任何证据。 毕竟皇后都说自己痛了,你就不能说她不痛。 宁遥思来想去,还是先决定去探一探。 她找了朝阳宫的羽棠,约她晚上在御花园边上的杏林里见。 羽棠是皇后宫里的粗使丫头,和原主紫芙打小认识,一同长大又一起无奈进宫,感情深厚。 在原主紫芙离宫去椋城时,她还眼泪汪汪地拉着紫芙的手说了好一通。 这些日子「紫芙」回宫,被皇后责罚磕破了头,又被「赏」给了殷绥以后,她还来找过「紫芙」好几次,送了不少治疗伤痕的药物给她。 宁遥到杏林的时候,羽棠已经在那儿等她多时了。 见宁遥来了,她微微低着头凑到她耳边,低声道:「你问我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 「我没有什么贴身伺候的机会,虽说能瞧见皇后娘娘,但也只能远远地瞧上几眼。」 「不过皇后娘娘的确在床上躺了好些日子了,远远瞧着脸色也不太好。」 宁遥点了点头:「如此,便多谢你了。」 羽棠反倒是拉着她的手叹了口气,声音怯怯:「你……在九皇子那里还好吗?」 见宁遥应了,她又道:「九皇子处境艰难,你何苦要……倒不如我替你去找竹苓姑姑求求情。」 「你也不用担心银子,我那儿还有一些,若是能求了竹苓姑姑替你说话,皇后娘娘又最是仁善,想来不多时便会消了气儿,想起你的好来的。到时候咱们也能继续呆在一起……」 宁遥回来时,夜色已深了。 景福宫的灯也已经熄了大半,从远处看过去,暗的地方多、亮的地方少。 她本想先悄悄溜回去睡觉,免得吵醒了其他人,可没成想她经过外殿时猛地被人叫住。 「姐姐。」 殿内只点着一盏孤灯,少年坐在孤灯之下,唇角一勾,脸上笑意清浅,好看的丹凤眼微微眯起。 「姐姐方才去哪儿了,怎么现在才回来?」 「也没去哪儿,」宁遥答得坦荡,「我刚刚去见了之前的一个朋友。」 「你白日里不是问我皇后这病吗?我去找朝阳宫里的朋友问了问。」 殷绥微微松了口气。 他方才去了冷宫,回来经过杏林时,却见她和朝阳殿一个宫女在一起,举止亲密。 那女子还附在她耳侧,不知对她说了些什么。 他当时还以为…… 只是这样便好。 殷绥缓缓笑了起来。 他直勾勾地看着她,眼睛眨也不眨地问道:「那姐姐打探出来些什么没有?」 宁遥沉默着摇头。 「没有。羽棠在只是个粗使宫女,很少进内殿,消息不是很灵通。」 殷绥垂下眼来,长长的羽睫在眼窝处投下了道阴影。 他方才也见了全顺。 回了皇宫以后,全顺的日子越发不好过起来,短短几日头上身上便添了不少的伤,连走起路来都是一瘸一拐的。 他告诉殷绥,皇后的病确有蹊跷。 「我偷了些熬过的药渣,瞧了,都是些平日里喝的温补的药材。」 殷绥眼里闪过一丝疑窦,面上却丝毫不显,反而轻笑道:「只要姐姐有这个心,阿绥就心满意足了。」 次日一大早,殷绥照例去了朝阳宫给皇后请安。 朝阳宫里泛着股浓重的药味。 他还未走进殿内,便听得里头传来一道又一道的咳嗽声。 等进了内殿,之瞧见皇后病歪歪地倒在榻上,脸上还带着因为剧烈咳嗽而泛起的潮红。 瞧见殷绥过来行礼问安,她也只是懒懒地摆了摆手。 殷绥坐了不过一刻,就见有宫女端着汤药过来侍奉。 「娘娘,该喝汤药了。」 来人正是昨儿夜里他见到的那位羽棠。 皇后先接了药,瞧见是她,忙喝道:「怎么是你?竹苓呢?」 「竹苓姑姑去尚衣局了。」 「奴婢刚熬了药,见竹苓姑姑和丹栗姑姑都不在,就自己端了过来。」 皇后摆手:「好的,本宫知道了,你下去吧。」 「绥儿也下去吧,都说了这几天让你别来平安了,可别把病气传给你。」 殷绥应了声,也跟着退下了。 离开前他特意又看了那个宫女一眼——他分明能感觉到,刚才那宫女瞧见他时的紧张。还有她侍奉汤药的规矩,瞧着也十分娴熟,不像是第一回的样子。 他想到宁遥对他说的话,眉心微皱。 皇后这病一病就病了小半个月,朝堂上对此事的议论从未停过,都说是祖先预警,非是吉兆。 直到半个月后,平定西北战事的大将军江照身体痊愈,硕武帝加封其为正一品征西大将军并有意在宫中设宴款待以示荣恩后,人们才转而恭贺起陛下的圣明、大将军江照的年轻有为来。 这江照说来也是个传奇人物,无出身无背景,却在从军之后短短五年频频立功,爬到了车骑将军的位置。此番西北战事更是立了头功,官至骠骑将军后又被硕武帝加封为正一品征西大将军。 一时间朝堂上下喜气洋洋。 连殷绥脸上都多了丝喜气。 ——人们只知『江照』无出身无背景,全靠自己在沙场上摸爬滚打、死里逃生,才换来的将军之位。 可殷绥却清楚,江照是他的表舅舅,是他伯祖父年轻时与娼妓春风一度后生下的私生子。他伯祖父因为这件事情累了名声,向来不喜这个孩子,连江家的族谱都不让他上。 江照虽在江家长大,却受尽鄙夷,只有殷绥的母亲江靖柔怜惜他孤苦,常常去看他,给他送些衣服吃食。 殷绥有心想见江照一面。不仅为了江家,更为了他自己。 江家『谋逆』一事一直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他心头。 江家世代从军,三代五将,战功赫赫,又世代忠君,只愿盛世清明。 他不相信江家会突然谋逆,更不愿自己母亲连死都背着『逆臣之女』的名号,连自己也受了牵连,失了母家的支持,在宫中步步维艰。 只是这见面的时机...... 硕武帝盛年已过,渐渐开始有些懒政倦政,可对于兵权向来是极为在乎的,更忌讳皇子们私结边关将领。 殷绥思索了会儿,又想到宁遥和羽棠见面的场景,心生一计。 他叫全顺打探了江照入宫述职的具体时间,又求了宁遥在江照进承明殿前找个时机截住他,给他带个口信儿,就说请他在三日后前往京郊的茶楼里,共商大事。 为此,他特意选了个合适的时机对她再三嘱托—— 「姐姐,此事事关重大,阿绥身边实在没有可信之人,只能拜托姐姐帮我这个忙了。」 「我把自己的性命都交托在姐姐身上,姐姐可一定要替阿绥做好。」 他直直地望进宁遥的眼里,一双黑润润的眸子里暗流涌动。 姐姐,你可千万千万......不要骗我。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qiongjiezx.com/qjfz/189521.html |
当前位置: 琼结县 >皇觉寺为了迎接圣上的到来,提前好几天便开
时间:2024/4/28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雷电预警6月7日琼结县气象台发布雷电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