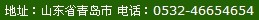|
作者:郭建立 (图片来自网络)
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疾驰的列车一路向西,向西,上升,上升。
鳞次栉比的楼群渐渐少了,起伏连绵的山岭渐渐多了,骤暗忽明的隧洞一个连着一个。
尽管乘车需要46个小时,但却没有漫漫旅程的倦怠,我把鼻尖贴在车窗上,屏息凝神地望着窗外倏忽远去的风景。我知道,心仪已久的西藏正一点点近了,近了。
在接到去西藏的通知后,我的心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那就是李娜、韩红歌声中所描绘的地方:高原、牦牛、雪莲、毡房、哈达、青稞酒……还有那永远都透着几分羞涩的高原红;紧张的是,听说每一个初进藏的人,都要接受高原反应的考验。自己能经受住考验被雪域高原欣然接纳吗?
兴奋着,紧张着;紧张着,又兴奋着——那让我陡然萌生起初恋情怀的雪域高原呀!
(一)
经过青海路段的时候,面对几乎寸草不生的茫茫戈壁滩,我的心不由一凉,莫非我所要走进的就是这样一个无比荒凉的地方吗?不过这种担心很快就被打破了,车窗外的风景越来越美,金灿灿的阳光下,是积雪皑皑的山岭;山岭的怀中,忽而是正在泛青的草原,忽而是把天光云影融为一体的淡蓝色的湖泊。在草原上纵横的河流,清澈见底,闪着粼粼的光芒。尤其看到那一群群机敏伶俐的藏羚羊和安详宁静的牦牛,车上的旅客都欢呼惊叫起来。带相机的旅客急不可耐地拿出相机,贪婪地拍起了照片,“咔嚓,咔嚓”的声音响成一片。
对于一个在内地生活,习惯了熙来攘往、人潮涌动场面的人,面对杳无人影的地方,心中还是激起强烈的期待,期待看到人的身影。毕竟只有人才能显现出最强烈的生命意识,最浓烈的生活气息。路上见到几群护路的工人,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他们已热情洋溢地向我们欢呼招手,我们也激动地热情地向他们招手致意。从来没有体验到人与人之间原来是这样地依恋,这样地容易亲近。
在接近拉萨的地段,又一种景象把我震撼:远远的一条公路上,几个身着藏服的人,不停地向着前方合手叩拜。他们叩拜的方式不是屈膝下跪,而是把整个前身贴在地面上,循环重复,站起又伏下,伏下又站起。有知情的游客介绍说,这就是西藏的“磕长头”,路程最长的要磕一年多时间。“磕长头”是藏族人对佛祖最虔诚的礼仪,每个人一生要磕够10万个。我惊愕地眺望着“磕长头”的人,似乎可以看到他们在夕晖照耀下肃然宁静的脸庞。那脸上尽管刻满风霜的印痕,但却洋溢着自信、满足和期待。 (图片来自网络)
忽然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是呀,对于心仪已久的梦想,不就应该拿出朝圣者的勇气和志向吗?无论面对怎样的考验,都应该一往无前、永不回头。
啊,我的雪域高原,我愿把所有的一切都抛在身后,以赤子的胸怀去紧紧地拥抱您,去接受您紧紧地拥抱!
(三)
下火车已是夜幕降临,灯火阑珊。导游把一条条哈达献给我们,送上一声声“扎西得勒”的祝福,我们也以“扎西得勒”相回应,一股陌生但却炽热的暖流顿时涌遍全身。
亮起的灯火只能勾勒出拉萨市影影绰绰的轮廓,四面的群山黑黝黝地像巨大的剪影。市区最醒目的是布达拉宫。坐落在山顶之上巍峨壮观的布达拉宫,在灯火的笼罩下,透出无尽的神秘,让人内心涌起马上就想走进的冲动。
导游被我们几个性急的人给逗乐了,笑着安慰我们,先休息,按照行程安排,要几天时间呢。在这里旅游,急不得,因为大多数从内地来的游客都会有高原反应,要多休息,多喝水,不能作剧烈运动。
然后,导游简要介绍了西藏的概况:西藏面积多万平方公里,是一个以藏族为主的有多万人口的自治区。境内平均海拔在米以上,海拔米以上的高峰有50多座,其中米以上的有11座。气候寒冷,气压低,空气稀薄,素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之称。
我核算了一下,西藏的面积与我们所在的县相比,是全县面积的倍,而人口仅为4倍多。真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说到山,在我们那个地方,海拔~米的就可煞有介事地称之为“山”,如果与这里的山相比,应该算是“小土堆”“小泥丸”了。
不到西藏,怎知道什么是博大?什么是辽阔?不到西藏,怎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山峰?
(三)
这就是西藏,天是湛蓝的,蓝得像染料染过一般;云是洁白的,白得像一大团漂浮的棉絮。阳光也不只是灿烂,而像携带着千丝万缕的金线从高空直射下来。只是看看沐浴着阳光的楼群、柏油路,都会让你不由得眯起眼睛。这让我想起了孩童时代用好奇清澈的眼睛看到的一切,那时的天空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亮得逼你的眼。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亮的光景不见了,总觉得到处灰蒙蒙的,不知道是眼睛近视的缘故,还是天空真的没有那么亮,云没有那么白,阳光也失去了锐利。湛蓝的天让我想起奶奶印染的蓝布衫,洁白的云让我想起了妈妈手中弹的棉花。 (姬天剑/摄) 到拉萨如果不看大昭寺、布达拉宫大概就像到洛阳不看龙门石窟、白马寺一样。
随着导游的旗帜,走进市区,我便强烈地感受到西藏浓厚的佛教色彩。在街头,几乎看到的每一个藏民,手中都不停地转动着藏经筒,拨弄着佛珠,口中念念有词。
大昭寺建于公元7世纪,据说是松赞干布、尼泊尔赤尊公主及唐文成公主共同兴建而成。寺门朝西,有面向西天佛地之意。主殿共4层,糅合了汉、藏、印度和尼泊尔的建筑特色。释迦牟尼佛殿是全寺的精华所在,供奉着与文成公主随行入藏的释迦牟尼坐像。围绕大昭寺有一个叫“八廓街”的环形市集街道,随着大昭寺的落成而逐步兴旺,形成长约米既是转经道又是商贩云集的购物区。游“八廓街”须随朝拜的藏族人依顺时针方向行走。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7世纪,由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而建,后毁于公元8世纪。公元17世纪,五世达赖用了3年时间重建。宫殿主楼高米,共13层,由红宫、白宫两部分组成。红宫居于布达拉宫的中部,主要建筑是历代达赖喇嘛的灵塔殿和各类佛堂;白宫是历代达赖喇嘛起居和理政的地方。
由于自己对佛教知识了解得很少,游览这两个地方,能记住的东西很有限,只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两个地方,是千余年来藏族人民全部心血、汗水和智慧的结晶,其间价值连城的宝物比比皆是,让人目不暇接、惊叹不已。
据说,文成公主入藏嫁松赞干布,从长安出发时年仅18岁,见到松赞干布已是21岁。遥想当年,长路漫漫,马铃叮当,数年的光阴,对于一个入藏把终身相托的女子该是多大的考验。在她的身后,岂能无故国的牵挂,岂能无爹娘含泪的目光。但为了藏汉的融合,为了世代的友好和平,她甘愿把一切都抛弃了。面对文成公主的塑像,我似乎一下穿越了千余年的光阴,看到了她青春的容颜,看到了她教藏族人民耕织的身影。我深深鞠躬,眼眶发热,内心一遍遍地呼唤:可敬的公主,你是否还认得我这隔了千年、隔了万里的故乡人;是否还记得浸染了中原泥土芳醇的乡音?
在大昭寺、布达拉宫随处可以看到不停朝拜的藏民,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还有身体残疾的。这时我才看清,他们的手掌上套着合掌大小的木板,膝盖上绑着用布做的护膝,朝拜时,双手合掌,先举过头顶,再放到唇边,再放过胸口,然后,双手伸直向前,身子俯冲贴地,额头叩打地面。从他们的衣着可以看出,他们多数风尘仆仆经历了漫长的跋涉。尤其那些年迈体弱和身有残疾的人,每一次叩拜都异常吃力,但他们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一招一式,一丝不苟。“虔诚”两个字,早已熟悉;“虔诚”两个字,也用得很多,只是当面对“磕长头”的藏民,你才忽然发现,过去对“虔诚”的认识和理解是多么的肤浅、稚嫩。或许真正的虔诚,就是这种不含一丝杂念的能够超越生命的信仰。
(四)
进入西藏的游客,大概都和我一样,最急于了解的是“达赖喇嘛”和“班禅”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转世灵童”又是如何确定的。
导游讲,“达赖喇嘛”和“班禅”是西藏并列的两大宗教领导,“达赖”是蒙古语“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上人”的意思,也可翻译为“活佛”。“班”是梵语,“禅”是藏语,合起来是“大师”的意思。西藏划分为前藏、后藏,达赖喇嘛负责前藏的宗教事务,班禅负责后藏的宗教事务。确认“转世灵童”,一般是根据活佛生前的预示、遗嘱等线索,通过降神、占卜、观圣湖的方式,占知其转世的方向、地点,然后派人化装秘密寻访灵童,再对寻访的幼童进行观察、试验,以作筛选定夺。
在历代达赖喇嘛中,功德最高的为五世达赖喇嘛,他花费3年时间组织重修了布达拉宫,并推行了政教合一的管理模式;最富有个性魅力的当属六世达赖仓央嘉措。 (图片来自网络)
相传五世达赖66岁在布达拉宫圆寂,他手下的总管自作主张隐瞒了达赖喇嘛的死讯,秘密派人四处寻访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在山南的措那地方,他们找到了一个聪明可爱的儿童,认定他是五世达赖的转世,把他接到措那城堡悄悄供养起来,到了15岁时,在布达拉宫大殿坐床。他就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仓央嘉措不喜欢被人当神佛一样供养在布达拉宫,每天从早到晚没完没了地诵经礼佛。他穿上俗人的衣服,戴上长长的假发,化名唐桑旺布,溜到八廓街或布达拉宫下的雪村,找男朋女友玩耍,享受世俗生活的快乐。仓央嘉措还在布达拉宫后面林园的湖中小岛上,修建了一座名叫龙王潭的精美楼阁,在此邀请拉萨城里的青年男女,唱歌跳舞。在龙王潭,仓央嘉措结识了一个来自琼结的姑娘,名叫达娃卓玛。达娃卓玛容貌美丽,性情温柔,嗓音甜美。仓央嘉措和她一见倾心,白天一起歌舞游玩,夜里常常幽会。后来仓央嘉措发现达娃卓玛好些天没有到龙王潭来,给她捎信约会,却没有回音。他亲自到达娃卓玛住处拜访,达娃卓玛家已是人去楼空。从此,仓央嘉措再没有见过达娃卓玛。达娃卓玛成了他的梦中情人。在苦苦的思念中过了几年,仓央嘉措就圆寂了,去世时年仅24岁。仓央嘉措的行为看起来似乎离经叛道,让佛家难以相容,但他写的一些诗歌却代代流传。他反映自己过着活佛和俗人双重生活的诗歌中,有两首是这样写的:
在那东方山顶/升起皎洁月亮/年轻姑娘面容/渐渐浮现心上
黄昏去会情人/黎明大雪飞扬/莫说瞒与不瞒/脚印已留在雪上
……
常想活佛面孔/从不展现眼前/没想情人容颜/时时映在心中
住在布达拉宫/我是持明仓央嘉措/住在山下拉萨/我是浪子唐桑旺布
……
听着仓央嘉措的故事,让人不由想起了“词帝”李煜,想起了《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这世上大概有两种人最难做:一种是为了整个世界,忘掉内心的一切;一种是为了内心的一切,忘掉了整个世界。面对这两种选择,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真的是无法评说。仓央嘉措的诗歌一下化成了缠绵悱恻又弥漫着淡淡哀伤的旋律在耳畔久久回响,让人隐隐作痛,一声长叹。
(五)
高原反应说来就来了。那是在世界上最高的湖泊——纳木措遇到的。
纳木措湖面海拔米,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纳木措在藏人心目中具有非常神圣的地位,每逢藏历羊年,朝圣者不远千里前来参加纳木措盛大的转湖节,把身上带的宝石、绿珠纷纷抛向湖水中,以示对湖水的敬意。
在湖的旁边有出租马匹和牦牛的,我们旅行团很多人忘了导游不要做剧烈运动的叮嘱,,纷纷骑上马匹和牦牛,绕着翠绿的湖水拍照留念。在梦想中,我曾多次骑上骏马,在无边的草原驰骋,一旦真的骑上马背,才知道离疾驰的境界相差十万八千里。马被牧人牵着,走得很缓慢,但骑在上面,感觉身子左右摇摆,似乎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只能紧紧地拽住缰绳,两腿绷直蹬住脚镫,故作镇定地挥舞红帽,勉强定格一帧虚假的翩翩英姿。
导游讲,赛马节是当地最具有民族和地区特色的项目。每年藏历七月初起,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而来,参加一年一度的赛马节。骑马的高手在疾驰的马上可以做各种高难度的动作。有的在疾驰的马上俯下身很轻松地就把摆在地上的哈达捡起。导游卖了个关子,让大家猜猜赛马获胜者奖什么?有人说奖羊,有人说奖牦牛,有人说奖马,还有人调侃说奖美女。导游都摇摇头,笑着说,奖拖拉机。
等疯足玩够坐上车,高原反应就来了,心虚气短,后脑勺隐隐作痛,每咳嗽一声,感觉脑后的筋就像被人扯了一下。看看车上的其他游客,有的蜷缩着,有的皱着眉,有的不停地揉着太阳穴。幸亏有几名游客提前有准备,拿出抗高原反应的红景天、丹参等药,分发给大家,相互关切地询问着、安慰着。一个旅行团就是一家人,山美水美离不开情浓心美。
(六)
游览的最后一站是林芝。林芝被人们誉为西藏的瑞土,西藏的江南。
从拉萨到林芝有多公里的行程。车窗好像展开了一幅连绵不绝的画卷:时而青山连绵,时而草原辽阔,时而激流奔泻,时而油菜花一片金黄。当然最美的要属那些综合性的风景:高高的篱笆围着广阔平坦的牧场。牧场里是成群的牛马羊。牧场的尽头是云雾缭绕的高山。高山的下半部,覆盖着浓密的林木,山顶则是终年不化的积雪,似乎给高山戴上了一顶璀璨夺目的银冠。山脚下,是一座座大屋顶式的农家山庄,那涂染或红或蓝的铁皮顶盖格外抢眼。绿的草、青的树、白的雪,悠然的牛群、马群、羊群,新颖气派的农庄,构成了一幅巧夺天工、摄魂夺魄的画卷。如果深深呼吸一下,似乎可以闻到青稞酒的芬芳。 (姬天剑/摄)
在林芝主要游览了巴松湖和雅鲁藏布江两个景点。巴松湖海拔米,面积37.5平方公里,湖水平均深度为60多米,湖呈新月状,湖面开阔,湖水如镜,山抱着湖,湖绕着山,湖光山色相融,让人如痴如醉。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以世界上最深的峡谷而著称,并有世界上落差最大的垂直地貌分布。海拔米的南迦巴瓦峰就矗立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内侧。导游讲,峰顶云遮雾罩,难见其顶,只有运气好的人才能见到。我们回程时,奇迹发生了,远处的云雾渐渐淡开,慢慢地,一个洁白的山峰露了出来。先是一支尖削的山峰直刺蓝天,随之一道山梁连着尖峰,跃上云端。哦,南迦巴瓦峰赫然显露于我们的眼前,它卧在云雾之上,如梦如幻,好像让人看到了凌霄宝殿,只要一声呼唤,就会有天兵天将以雅鲁藏布江一泻千里的气势,从天而降。
去林芝途经阿沛庄园,我们还参观了一家农户。这的确是农户,但你不敢相信这是农户,两层的小楼坐落在花草丛中,走进楼内,从客厅、卧室,到厨房,乃至家具、楼梯,不仅设计匠心,并且都饰以精美的图案,洋溢着浓厚的艺术气息。没到西藏之前,在电视上看到牧人,总是把他们与粗犷、豪放联系在一起,想不到他们竟有如此精致、温婉、细腻的一面。
走出农家,大家要在庄园前合影留念,刚刚摆好姿态,只听见旁边传来一声提示“茄——子——”仔细一看,原来是村子里一位藏族老人在冲我们吆喝,大家顿时笑成一团。老人边笑边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去。何止是知道“茄子”,旅程中,只要与藏民对话,无论老人、孩子,几乎没有任何语言障碍,他们懂得藏语、汉语,能够流畅地和我们对话,这让我们感到很惊奇,也很惊喜。
另外,在沿途的农家屋顶上,山腰、河畔都能看见五彩的经幡。据说,这是藏民借助风来读经,风吹一下就是读经一次。在藏族人心中,山、水、风、树,乃至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都连着自己虔诚的信仰,都需要用敬畏之心去对待。
月亮升起来了,一弯清新的月亮挂在湛蓝的天空。清辉下,连绵起伏的群山远了,淡了;草原上吃草的羊马牛也温顺地聚拢到一块儿;毡房里升起袅袅炊烟,飘来酥油茶的清香。
守着这么空旷的草原,他们不感到寂寞苍凉吗?
导游笑了,说,牧民们过去成年累月就不用花钱,他们住的是牦牛毛织的帐篷,吃的是牦牛肉,喝的是酥油茶,点的是酥油灯;闲了,就对着他的牛、羊,弹琴、唱歌,他们没有寂寞,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寂寞。
我忽然想到,在我们出发的都市里,此刻一定是霓虹闪烁,夜市上熙来攘往,人们在喝酒,在唱歌,只是不知有多少人饮下的是寂寞,唱的也是寂寞。 (图片来自网络)
五天的西藏之游要结束了,当飞机把我们载上云端,我陡然涌起难舍之情,透过舷窗我不断向下张望,希望再看一看这片美丽而又神秘的土地。我知道,我所了解的只是这广袤大地上微不足道的一角;我不知道,我何时能够再次踏上这片土地。
西藏,如果愿意,请把我的心留下吧,留在高原上,开成一朵圣洁美丽的雪莲花。 作者简介:郭建立,洛阳新安县人。新闻工作者,文学爱好者。出版有个人新闻集《那山·那水·那人》,散文集《静静的月亮河》。 郭建立赞赏 人赞赏 长按北京安全治疗白癜风医院白癜风治疗用什么方法好
|
当前位置: 琼结县 >郭建立在世界屋脊上行走
时间:2018/9/20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最新2018西藏公招已报名1454人
- 下一篇文章: 卖室友第四季第一期你等南风吹,我等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