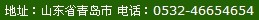|
附录一:方国瑜《彝族渊源与古羌人的关系》(节选)
彝族祖先从祖国西北迁到西南,结合古代记录,当与“羌人”有关。早期居住在西北河湟一带的就是羌人,分向几方面迁移,有一部分向南流动的羌人,是葬族的祖先。究竟彝族与羌人有何等关系,不详于记录,但我们还可以从民族学性质或语言学性质来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语言的亲属关系与族的亲属关系是有关的,虽然不是唯一的,但是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古代羌人的语言记录,有《白狼歌诗》三章,一百七十二字,是很重要的资料。这三章歌诗是在公元第一世纪汶山以西的白狼部落献给汉朝的,其经过详见《后汉书?西南夷传》和《东观汉记》。汶山即《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说“以冉駹为汶山郡”,司马迁称其居民为“氏类”,即羌人的支系,现在住居在川西的羌族,即冉駹的后裔。白狼就是冉駹西部的部落,歌诗三章为当日羌人语言的记录。据近人研究白狼歌诗的结果,有认为是彝语的前身,有认为是古代的纳西语,有认为与藏语最相近,也与普米语、西夏语相近。从语音、语法和词汇作比较研究,这几种语言都与白狼歌诗相同或相近。其他如傈僳语、拉枯语、哈尼语也与白狼语相同或相近。这是由于这几种语言是同源的,也就是这几个族是同源的,从白狼歌的语言作比较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不能如丁文江所说“白狼文是倮倮文的前身”,但倮倮语与白狼语,亦即彝语与羌语有最亲密的亲属关系,则是比较明显的。
至于古代羌人的生活和文化特征,见于记录的不多,《后汉书?西羌传》和《西南夷传》筰都夷、冉駹夷所载,有些是一般地区可以有的情况,如说“累石为室”、“披毡为衣”“以射猎为事”,这是人类利用自然来谋生活的手段,不同的族可以是相同的,又如“杀人偿死”、“嫁女得高赀”(《广志》)之类,除非特殊情况之外,不能根据这类事来说明不同族之间就一定有相互关系。但古代羌人所具有特点的事,我们可以加以研究,其比较突出的,如《西羌传》说:(1)“以父名母姓为种号”;(2)“十二世后相与婚姻”;(3)“父段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鳌嫂”;都夷说:(4)“言语多好譬类”;冉夷说:(5)“死则焚其尸”;(6)“贵妇人,党母族”。这些古代羌人生活上的特征,与彝族比较,大概相同,不能说是偶然,而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至于《西羌传》说羌无弋妻“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那是个别的事,而且是后来才有的,有关彝族记录没有提到此种习俗。
其次,关于族名,南中葬族有专称,但也称之为羌,如《后汉书?西羌传》说“或为旄牛种,越嶲羌是也”。越嶲在大渡河以南,古代彝族的主要聚居区,是羌的一支。又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蜀汉时“移南中劲卒青羌万馀家于蜀”。是从建宁郡调去的,建宁在滇池曲靖区域,也是古代彝族主要聚居区。这两地区的居民称之为羌。又滇为部落称号,《后汉书?西羌传》载羌人酋豪之名有滇良(子滇吾,滇岸),滇零、滇那,以滇为号。又《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王名常羌,以羌为名,也可能是羌族共有的情况。从名称上,可知所谓越供夷,建宁夷与羌人有关。总之,从彝族迁移的方向以及语言、生活、文化、名称的特点,都与古代羌人有关,“彝族渊源出自古羌人”的提法是可以成立的。(选自方国喻《葬族史稿》14-15页)。
附录二:吴恒主编《彝族简史?族源问题的探讨》(节选)
彝族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惟史书上对彝族源流问题没有系统的阐述,因而,一百多年来,彝族族源问题,就成为中外学者聚讼不休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的有如下数说:
(1)东来说。有人认为葬族先民原是楚国人,居住在洞庭湖流域。《左传?桓公十三年》载称:“楚屈瑕伐罗。”罗与卢两部联合起来大败楚军。后罗、卢两部随楚将庄蹻入滇,然后播迁西南各地,历久演变,即成为今日的彝族。解放前彝族被称为“罗罗”,即“罗卢”的对音。(2)西来说。有人认为彝族来自西藏,或来自西藏与缅甸交界的地区,语言和体质特点的相似,是彝族与藏族关系密切的明证。(3)南来说。认为彝族祖先是古越人或古僚人。持此说者把《北史?僚传》所载僚人习俗归纳为18项,认为有许多项跟葬族的习俗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持此说者有的甚至还认为彝族最初系来自南方,属于马来人种。(4)北来说。认为彝族祖先在远古时期原住在“旄牛徼外”,后迁到“邛之卤”,然后播迁金沙江南北各地。古羌人便是葬族的祖先。(5)濮人说。认为彝族先民是古代的濮人,“今称倮倮”。(6)云南土著说。认为云南自古便是彝族的发祥地,今川、黔、桂各地彝族皆发源于滇。(7)卢人说。认为“周武王牧野之誓有卢人,滇之倮即卢之转音”(8)卢戎说。认为葬族先民“卢鹿部”,可能与春秋时的“卢戎”有关。
各种说法都值得研究。“民族并不是种族的人们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人们共同体,而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解放后30多年以来,通过葬族地区社会历史的调查和对彝族史的研究,一个比较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看法是:彝族是从“旄牛徼外”南下的古羌人这个人们共同体为基拙,南下到金沙江南北两岸以后,融合了当地众多的土著部落、部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选自《彝族简史》(吴恒主编)9-10页)。
附录三:孔祥卿《彝族的历史来源》(节选)
彝族或者说彝语支民族源于古羌人的南下,这基本上已成定论,尽管也有一些反对意见,尚不能撼动这一说法的根基。方国喻《彝族史稿》列出的火葬、父子连名制、同氏族若干代分支后互相通婚、党妻族、“言语多好譬类”、骑马披毡等葬族和西羌共同的习俗(方国喻)),是彝族和古羌同源的有力证据。羌人是游牧民族,迁徙不定,向东迁徙的一支融入华夏族,向西迁徒的后来成为吐蕃即今之藏族,向南迁徒的羌人种类最多,成为今彝语支各民族。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彝族土著说。考古资料证实,云贵高原一百多万年以前就有古人类活动,考古学上的“元谋”人、“丽江”人都属于早期智人,比“北京”人的时代要早得多。因此,童恩正先生说:“包括中国西南在内的亚洲南部,有可能就是人类起源的摇篮”(童恩正)。刘尧汉先生说,如果说彝语支民族都是从北方来的,那么,当地的土著哪里去了?很难相信羌人南下之前云南这片土地上没有土著民族。相反,北方的氐羌倒可能是从云贵高原迁去的(刘尧汉)。
我们同意人类起源多源说,中国大陆的北方和南方云贵高原都是人类的起源地。也确实应该相信云贵高原早有土著民族,但远古时期的土著民族不一定是现在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直系祖先。比如,今居住于两广、贵州、云南甚至越过边境直到越南、泰国等地的伺台语族的人民,原是居住在长江流域的“百越”民族,先秦时期汉人的南下,使得他们向南向西迁徒;而他们更古老的祖先,则有可能是五六千年以前居住于今山东及其周围地区(江苏、安徽北部、河南东部)的古东夷人。
古代的云、贵、川南一带的土著民族可能是古文献中记载的“濮”人,他们是从事低地农业的民族。古老的葬文文献中,记载了彝族的先民在迁徒的过程中,不断地与濮人发生战争、征服濮人、赶走濮人或与濮人融合的故事。彝文“濮”是土地的意思,可以认为“濮”就是土著民族,也可解释为耕种土地的农业民族,与游牧的氏羌民族不同。古代的羌族生活在西北至西南的广大地区。甲骨文中有“羌方、伐羌方、往羌、获羌”等字眼,《诗经?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不敢来享,莫不敢来王。”说明在公元前16世纪左右的商朝初年,氏羌部落是在商朝周围,受商朝统治的一个民族。《说文解字?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
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黄帝族原来居住在西北方,过着“迁徒往来无常”的游牧生活。黄帝族应是羌的一支,后来黄帝族进入中原,但黄帝与西部羌族的关系仍很密切。《史记?五帝本纪》、《山海经?海内经》都说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即今四川西部的稚砻江。
注:作者孔祥卿,女,年出生于河北辛集,汉族,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和葬语言文字研究。(昭通彝族简史无语_新浪博客)。中国古代民族简介(西南篇) 1、蜀。古族名,国名。氐羌族之一支是从叟人中分化出来的。分布在四川偏西地区,曾参加武王伐纣之盟,到蚕从时始称蜀王。以后杜宇(望帝)禅位于开明(杜宇相)迁成都。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年)灭于秦。秦于其地置蜀郡,主要从事农业,以后蜀人与入川之秦人,逐渐融合,成为后来汉族的组成部分。杜宇生于朱提(今昭通),教民务农,娶朱提梁氏女为妃,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囿苑。其后保子帝“雄长僚僰”,意即控制了滇、川、黔边僚人僰人地区。“有滇、僚、賨、僮、仆之富。其时,在蜀之西还有“徙”(在汉嘉今四川天全雅安)还有“邛都”(在今四川西昌、凉山)两个独立的大部落。 2、笮。古族名。春秋战国时分布在川西滇西北地区,是“六夷”的一个古老民族。后与南下的氐羌族融合。笮在今四川盐源、盐边及云南华坪、永胜、宁蒗一带。产名马名笮马,体形较小,但能负重有耐力,适应山间小路。为岁纳贡品。 3、巴。古族名,国名。《山海经-海内经》巴为太昊之后。《华阳国志-巴志》又说:巴为黄帝,高阳氏之后。主要分布在今川东、鄂西一带,廪君为著名首领。因以前居湖北长阳西北,后向川东扩展。因助武王克殷封为子国。称巴子国。为廪君蛮、板楯蛮、武陵蛮、江夏蛮(又称五水蛮)的先民。战国时,巴与蜀“世代有争”遂北向联秦,秦借口救巴,遣归仪,司马错率兵入蜀,蜀亡后,又灭了巴,苴(在今四川北部昭化一带)。东汉西晋时,廪君蛮与板楯蛮已逐渐融合称为巴人或賨人。汉末一部分巴人北上归附汉中的张鲁,以后,宕渠的巴人也北入汉中,曹*把巴人也迁入汉中,曹*把巴人迁到略阳与氐人杂处,又被称为巴氐。后来巴人与汉人的差别已逐渐消失,其余巴人和苗、瑶族融合。苴:蜀王封第葭萌为苴侯,命其居地为葭萌,因其弟私亲巴人,故蜀、巴世有战争。又说,苴,实为巴族之一支。其时,巴之四周降苴以外,还有賨、共、濮、奴獽、夷蜑诸蛮。奴獽、夷蜑均为被统治之国。“共”是賨的分支,是板楯蛮,七姓渠师龚姓之别称。 4、僰。古族名,国名。氐羌族的一支。“僰”是自称,又是他称。秦时滇东北的僰道(今宜宾)曾为僰候国的所在地,后来大量僰人沦为奴隶,称僰僮。秦汉修五尺道和西南夷道都以僰道为起点,向南延伸从会无(今会理)渡泸(金沙江)至高狼(今会泽、巧家)直至滇中,沿途均为僰人居住地区,称为濮人之邑。濮,古读为僰又称滇僰。《水经?汉水注》引地理风物志说:“夷中僰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这是因为僰族当时经济文化有较高发展之故。西汉末年朱提(今昭道)的僰人已修了“千倾田”,种植水稻。冶铜技术也较为发达。今滇中的通海,江川至石屏一带是西汉的胜休县,王莽为了镇压僰人把胜休县改为胜僰县。公元一世纪,僰人首领若豆,孟迁起义击败了王莽派来的二十万大军,可知滇中直到西汉末年乃是僰人的主要聚居地区。武帝设益州郡后,“靡莫三属”和“滇王”不再见于史册,是时滇国已衰,滇之名也随之消失。这一时期并没有大量僰人迁入滇中的记载,说明也是原业滇中地区的主要居民。 5、濮。古族名,又称仆人。魏晋南北朝称濮。唐称卜子蛮、宋元称蒲蛮,卜蛮。明清称哈喇,卡瓦、卡喇、崩龙,为现今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的先民。住在古云南西南部的濮人不是南方的濮人,也不是滇中的“僰人”,更不是春秋时参加武王伐纣和成王成周之会的濮人。古代元江因流经濮人居住地区故又名“卜水”。殷商时,卜人就向商王朝献“矮狗”(短狗),向周王献丹砂。直到明清时期,王朝仍规定顺宁(今风庆)的蒲蛮以矮狗(即短狗)为贡品。当时“儋耳、焦侥”也是濮人,后来分化为“卜子”和“望”两族。前者形成今天的布朗族,后者形成今天的佤族。又:相传古代南方百濮的一部到云南后也可能与云南的濮人融合。另一部或属巴或属楚,属楚的巴人,是近代布依、侗、水族的先民。 6、叟。古族名。东汉末至三国时,是滇池地区和滇东的主要居民。王莽镇压僰人起义的二十万大军,都是从天水、陇西、广汉、巴蜀等地征来,这些地区都是叟人住地。叟又称氐叟和僰人称氐僰一样。南中叟人主要分布于滇中,滇东及四川西昌一带,与秦汉时期僰人分布的地区大体相同。说明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近亲或继承关系。叟人大量移入滇中,是民族压迫的结果。僰的名称消失又和叟人大量南迁有关。原来以僰人为主的滇池地区和朱提郡(今曲靖)由叟人取代(今晋宁县晋城),滇池地区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7、昆明。古族名。汉晋时,居住在滇西滇东和滇中山区的“编发,随畜行徙”的一些部族,叫昆明诸种,或昆明之属。是云南境内人数最多和分布最广的民族集团。当时,汉人把云南境内各少数民族又泛称为“夷”或“夷种”。称大种曰“昆”,小种曰“叟”。与昆明人同时存在的还仍有嶲(音西)、笮、邛等同族部落。属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原始社会时期。他们多次阻断了汉武帝寻求通身毒(印度)的通道。东汉时,刘尚渡泸击“昆明诸种”追至不韦(今施甸)并在洱海和保山地区设西部都尉(后改为永昌郡),管理这一带的“昆明”人。住在滇池以东的“昆明”人,在他们住地都留有“昆明”这个地名。诸葛亮南征后,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青羌”,与交纳赋税的賨叟不同。他们当是住在山区从事游牧的“昆明”人,与住在坝区从事农耕的“僰、叟”人处于垂直分布状态。史载三国时云南有所谓“上方夷”和“下方夷”之分。“上方夷”即是山居的昆明人。西晋以后,朱提郡的“叟”人和“僰”人大量西迁,滇东遂成为“昆明”人的主要聚居地区。由于居住在“爨”氏统治地区的东部,后来又称为“东爨”。但族属上区别于“西爨”。蜀汉时,原居住在滇西的“昆明人”,又大量移居至滇中和滇东北与原来居住在那里的“昆明”人汇合。隋唐五代时聚居在滇东北的昆明人曾建立过“罗殿国”。“滇僰”西迁和“昆明”东迁,是东汉至隋唐时期民族迁徙的主流。 8、乌蛮、南诏。古族名,国名。唐时主要分布于今四川、云南南部、东部、贵州西部,为东爨、六诏的主要部分。属氐、羌氏。唐时以乌蛮为主体包括白蛮等族曾建立过南诏国。开始以蒙舍首领细奴罗建立大蒙国(贞观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以巍山为首府。开元年间其王皮逻阁在唐的支持下统一了六诏(蒙舍诏、浪穹诏、施浪诏、瞪赕诏、越析诏),遂建立南诏国,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市南?痛逦?,被封为台登郡王,后又封为云南王。六诏的统一,成为唐朝在西南抗拒吐蕃的屏障。天宝九年(公元七五0年)反唐陷姚州,臣服吐蕃,后屡败唐兵,将唐势力逐出云南。安史之乱后。又乘机北取嶲州南部地,继向周边僚蛮部落大事开拓。历史上叫西开“寻传”,其国土,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东至滇黔边界乌蒙、乌撒部,南抵红河上游,同时筑拓东城(今昆明市),以控东南,成为唐时西南一大强国。贞元十年(七九四年)又转而通唐反吐蕃,夺取了神州都督府址(今剑川、鹤庆、丽江、中甸一带)和昆明城(今盐源)。又南征“茫蛮、黑齿”等部,拓土南至女王国(今泰国南奔一带)。大历十四年迁都阳苴咩城(今大理市)。历传十三王,其中,十王受唐册封,前后共三四七年。唐天复二年南诏中兴五年(公元九0二年)为其清平官(宰相)郑回之后郑买嗣所灭。主要原因是连年用兵,曾西掠骠国,两陷安南、掠邕州、攻黔州。四次攻打越嶲、成都掳掠抢杀,民怒沸腾,终于引起广大奴隶和百姓起义,郑买嗣只不过利用了这个时机而已。 9、白蛮、大理。古族名,国名。段思平,出自白蛮大姓,世为南诏贵族。公元年,原通海节度史段思平灭大义宁国(南诏亡后,相继出现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3个小国),建立大理国。大理国基本上继承了南诏的疆界,段思平在位时作了一些改革,后为大臣杨义贞所代。仅四月,鄯善(今昆明)领主高升太起兵灭杨义贞,恢复段氏政权。继后,高升太骄横跋扈,遍封其子弟于八府、四郡,实际上控制了大理政权。公元年,段氏让位给高升太,高氏自立为王,号称:“大中国。”但是其他领主不服,起而反高。二年后,政权复归段氏,高氏任大理相。当时少数部族首领相继进行封建割据。37部中的于矢部(今曲靖地区东部和贵州的西南部)建立“罗殿国”,“些么徙”部(今曲靖地区南部和玉溪地区东部)建立“自杞国”。滇南各部则各自称为“特磨道”(今文山州),“罗孔道”(今红河州外),“白衣道”(今元江及附近地区)等等。当时在西双版纳地区还有“景龙金殿国”。这些大小领主都是后来土司的前身。不过,大理政权基本还是稳定的。一直与宋修好。宋王朝也于太平天国七年(公元年)大渡河上建造大船:“以济西南蛮夷之朝贡者”。为了加强与西南各族的政治经济联系,宋王朝还封大理王为“云南八国都王”。后来改封为“云南大理国主,统辖姚、嶲州界山前山后百蛮36鬼主,兼怀化大将军、忠顺王”。淳化五年,政和七年进一步册封大理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大理王”。宋末,大理国是南宋王朝抗御蒙古贵族西部战线的主翼。公元年大理将军高和统率云南各族人民在九禾(今丽江九河)打退了蒙古军队的进攻。在这次战争中,高和战死,至今九河地方还保着“白王塔”的遗迹。元灭南宋后于元宪宗四年(公元年)派军南下攻克押赤城(今昆明市)俘段兴智,大理国亡。大理国前后传22世,共年,大体和宋朝起讫的时间相同。白蛮是现在白族的祖先。宋时(北宋、南宋)均与大理国友好,无战争。大理亡后,滇东三十七部些么徙自杞国还对元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10、爨。古乌蛮、白蛮大姓,又是古地域名。魏晋南北朝时由今云南东部地区统治集团爨氏大姓演变而成。晋宋至隋唐时爨氏分为东西两部(均在云南东部),大抵以曲靖至建水为界。东部以乌蛮为主,西部以白蛮为主。元代一般以乌蛮为黑爨以白蛮为白爨。明以后爨则专指“罗罗”。西爨地区的白蛮,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以滇僰、叟、爨为主体而不断融合其它各族(主要是迁入这个地区的汉族)人民而形成的一个接受汉族文化较多的民族集团。当时住在洱海地区的“河蛮”及其附近的“松外蛮”,虽都是“白蛮”的一部分还不在爨氏统治的范围内。 东爨的乌蛮,主要居住着“昆明”人的许多部落。号称“昆明十四姓、乌蛮七部落”。主要有“阿竽路(今东川)、阿猛(今昭通)、夔山(今大关、镇雄)、卢鹿(今宣威及贵州水城西)、磨弥剑(今宣威、曲靖)、暴蛮”(今贵州兴义、普安),以及四川凉山地区的“勿邓”。到了唐宋时期,云南腹地的白蛮和乌蛮,通过异源同流和同源异流的不同途径,逐步形成今白族和彝语支的彝、纳西、哈尼等族。 11、滇。古族名,国名。滇又称滇僰,意为滇池的僰人。滇国以僰族为主体,在其辖境内尚有“昆明、叟”等族。氐,羌之别种,史称氐僰,亦称羌僰,当为氐羌族中的氐人。羌族又是从氐羌族分出来的一大族体,夏以前即有部分氐羌族南下四川、云南、贵州等省。战国时楚国农民起义领袖庄硚失败后率众数千经贵州入滇,征服了夜郎和滇池地区周围的莫劳浸,靡莫等数十个部攻,建立滇国,称滇王(在数十个部落中,以滇为最大)。庄硚原想在滇池地区蓄积力量,然后返乡与楚国统治者决一死战,后因秦遣司马错夺取楚国的黔中郡(公元前年),隔断了归路。起义者只好留下来同滇池地区的人民共同从事开发。史载“今西南诸夷,楚庄之后”,“自夜郎以西,皆庄硚余种”。实际上应该是不同族属的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滇国的形成比“巴、蜀”稍晚,其辖境相当于武帝时益州郡的范围。在滇国形成前僰族早就与内地有交往,在云南江川、晋宁、楚雄、祥云等县出土的青铜器文物其文化发展水平与中原一致,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2、掸。古族名,国名。掸国在古云南永昌郡西边(今中缅边境),早与中原有友好往来,掸人为缅甸东部掸邦的基本居民。居住在云南的掸人是傣族的先民之一。 13、附国。古族名,国名。地在今西藏地区东部,属汉代西南夷之一。《隋书?附国传》载:附国距蜀郡二千里,其境南北八百里,东西一千五百里,民二万户。产青稞、小麦、牛、马、金银。东与嘉良夷、南与薄缘夷,接西为女国,东北为党项。后为吐蕃兼并。附国为羌族所建之国。 14、女国。古族名,国名。六世纪中叶存在于青藏高原,保持着母系制,有关记载见《北史》、《隋书》。女国原名唐牦(葱茈)又说女国即羊同地处葱岭以南,北接于阗,东接吐蕃,有万余户,世代以两女王共管国政,王夫名金聚,不预政事。俗贵女轻男,妇女任吏职,男子为军士,生子皆随母姓。地产金、盐、朱砂、麝香、牦牛等,常售盐于天竺,售金器于吐谷浑,人民以狩猎为生。曾数次与党项、天竺争战,隋开六皇六年遣使朝隋,玄奘《大唐西游记》记此国为“苏伐刺拏瞿怛罗”(梵语)、意为金氏即产金之国。女国曾受吐蕃统治,后与羊同象雄合并,后为吐蕃兼并。与此同时,在青藏高原东边还有另一个女国,《新唐书》说它源于西羌,东女王号“宾就”。女官号“高霸”均为世袭。有户口四万余,大小八十余部落有汤、董等大姓,国人居层楼重屋散在山谷间。有文字。隋大业中(-年)蜀王杨秀曾遣使招抚,唐武德至天宝初(-年)数遣使朝唐,受唐封。天宝后转尊男子为王,受吐蕃役属。唐贞元九年又请附唐,此后其王虽受封于唐,但又结好吐蕃,故又称“两面羌”。其地望在今四川茂汶之西,雅安之西北,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中心在大金川上游。《新唐书》记南诏国称之为“西山女王”。又说象雄,羊同、苏毗、孙波乃女国之别称后均为吐蕃所并。 15、吐谷浑。古族名。亦作吐浑,鲜卑族的一支。首领吐谷浑是鲜卑慕容氏单于涉归之庶长子,最初游牧于辽河流域,后西迁至青、甘一带,始以吐谷浑为姓氏。国人多为羌人,实际上是羌化了的鲜卑族国,受汉文化影响也很深。南北朝时先属北魏、宋、齐。到夸吕时首领始称可汗,建庭于伏俟城(今青海省青海湖西岸),诸曷钵时附唐,为唐附马,封青海王。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历三百五十年,后来,余众迁灵州,再迁朔方,再后与当地汉族和其他民族融合。 16、吐蕃。古国名,族名。族人大多为羌族。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时,由住在青藏地区以雅隆部落为首的农业部落联盟所建。最早的首领为达布聂赛囊日论赞父子。在赞普松赞干布时降服苏毗(孙波)、女国(唐牦、葱毗、羊同、象雄)等部,自山南匹播城(今泽当、琼结)迁都罗些城(今拉萨)建官制,立军制、定法律、创文字,统一赋税,采用历法,重视农牧业,形成了以吐蕃国为中心的集权奴隶主贵族统治。原崇奉本教,后改信佛教(喇嘛教),九世纪中,赞普达磨死后,统治集团分裂,奴隶,属民起义,吐蕃瓦解,前后存在二百余年。至宋、元明初时,史籍仍沿称当地土著族,部为吐(土蕃,或西蕃、西番)。“蕃”是藏族的自称,是“本教”之“本”的音转。“吐”是汉语“大”的音转。是时“吐蕃”入唐,又自称“大蕃”。详见前唐吐蕃段。 17、夜郎。古族名,国名。属越僚系。初属南越,武帝灭南越,降汉,封为夜郎王。汉使至夜郎,王问:我与汉孰大?后世遂以“夜郎自大”讥讽高傲自大之人。传其先为漂流在江中竹筒中出生的婴儿,未出生前即啼哭不止,后为一女子抱至家中,夜半从竹中出,故名夜郎,长大后勇猛雄健,众推为首领,以竹为姓,以夜郎为国名。其领地在今贵州省黄平县以及云南曲靖地区东部和文山、红河东南部。夜朗附近尚有句(音勾)町、漏卧等国,后皆降汉。 18、大月氏。古西北民族族名。公元一世纪曾建立贵霜王国。最初游牧于敦煌、祁连山之间。后败于匈奴,迁新疆伊犁河流域以西,再后曹匈奴乌孙攻击又迁大夏(今阿姆河上游),大夏统治者南逃,大月氏建国,以蓝氏城为王庭(今阿富汗瓦齐拉巴德),封五翖(xi)候国。五翖(xi)候国为贵霜、休密、双靡、翖(音西)顿、都密,后贵霜兼并共他四部建立贵霜王国、首领丘却就。二世纪初成为北起花剌子模南至文迪亚横跨中亚和印度半岛的一个大国,首都在布路沙布罗(即富楼沙今名白沙瓦)。迦赋色迦王在位时,崇尚佛教、商业发达,远与西汉罗马帝国相交通。汉王朝仍称之为大月氏。三世纪时分裂,五世纪时为(口厌)哒所灭。其族属众说不一,未定,贵霜王朝灭亡后,大月氏人逐渐与本地土著融合,成为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一个民族。 19、小月氏。古西北民族名。是未西迁进入祁连山南山的一部份大月氏人。汉武帝时出山与汉人杂居,分为七个大种,住在湟中令居一带的称“湟中月氏胡”,另有一部居张掖的称“义从胡”,后融入羌族,语言服饰均与羌人相似。五代十国时曾建立仲云国,后为西州回鹘统管,北宋时又称大众熨小众熨。 20、乌孙。古西域族名,国名,其民多为大月氏种和塞种,最初活动在敦煌、祁连山之间,后被大月氏逐至匈奴。匈奴破月氏后,月氏又西击塞种、塞王南迁,乌孙又联匈奴攻月氏,月氏又西迁大夏,掠月氏余众遂居月氏地,后强盛不再服属匈奴。汉文帝后元三年(前一六一年),西迁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之间,都赤谷城(今吉尔吉斯坦共和国伊塞克湖东南伊什提克)。据《汉书-西域传》载:乌孙东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千八百人。相、太禄左右大将二人,候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地荞平、多雨、寒……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大宛接,南与城郭诸国接。居民以游牧为生。武帝元狩四年(前年),张骞使乌孙,说服乌孙与汉攻匈奴,匈奴闻乌孙与汉通怒欲击之。乌孙闻汉与大宛、月氏往来不绝,亦恐,乃遣使献马向汉通好,并求婚,武帝允之。先后遣宗室女细君,解忧公主嫁乌孙王,宣帝本始二年至三年(公元前72年-前71年),双方共同出兵20万大破匈奴,更立其外孙(解忧公主之子)元贵靡为大昆莫(弥),派长乐候常惠屯赤谷,属西域都护府统管。东汉衰落后,乌孙与汉关系日渐疏远。南北朝时,受柔然攻击被迫西迁葱岭北,与北魏关系密切。辽太宗会同元年(公元年),遣使入贡,后渐与邻族融合。近代哈萨克民族中尚有乌孙部落。乌孙本是匈奴的一支,有说是迁入西域之白种人,民皆深目高鼻,青眼赤须,其实是乌孙民众中多为大月氏和塞种人,而其统治层可能仍属北狄系统以狼为图腾的民族,不然乌孙被大月氏攻击,逃匈奴,匈奴也不会收留乌孙,更不会助乌孙反击大月氏。 秦汉时的西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指我国新疆及其以西包括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就狭义说,则指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我国新疆地区。从公元前3至2世纪起,东方各族——匈奴人、塞种人、大月氏人以及乌孙人陆续向西方大规模迁移,都是通过西域去的,西域是历史上与中西文化交通的走廊,又是各游牧民族角逐的场所,并先后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大小王国。 就狭义西域的地理形势而言,天山以南是四周高山环绕的一个大盆地。北有天山,南有昆仑山,东有祁连山,西有葱岭。只有在东北有一个缺口,通过蒙古高原和甘肃西北部。这个盆地,东西约长二千八百多里,南北一千多里,汉时,这个地区已变成一望无际的沙漠。发源于四周高山的许多河流,都注于大沙漠之中,于阗河与葱岭河汇合成一条自西向东的塔里木河,注入蒲昌海(今罗布淖尔)由于有塔里木河无数支流的灌溉,因此,沙漠中又有许多肥美的绿州,适宜于畜牧和农耕。 秦汉时代居住在这里的一些原始部落,占有沙漠中一块块绿洲,他们在这里建筑城廓,逐渐形成了许多号称“国”的小城邦。在大沙漠以南,自楼兰沿昆仑山北麓西行有条通道至莎车,约有十八“国”,总称“南道诸国”。自莎车向西南至帕米尔高原山间间,也有一些小“国”,总称“葱岭诸国”。在沙漠以北,自疏勒沿天山南路东行至狐胡,亦有十几个小“国”,总称“北道诸国”。沙漠南北诸国均以种植、畜牧为主,有城廓庐舍,故统称“城廓诸国”。“葱岭诸国”,由于耕种面积小,一般都过着随畜迁徙的游牧生活,天山以北,一直延展到西北利亚的极南边,都是高山深谷,其间有些小河和湖泊,是山岳地带。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有块很大的平原,即准葛尔盆地,气候湿润,水草肥美,最适宜于畜牧。汉初,分布在这里的小“国”,统称“山后诸国”。一个时期,天山南北诸国均为匈奴征服受其奴役。 大体上,自楼兰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自莎车向西南至帕米尔高原的各小国如西夜蒲犁、依耐、无雷……等。居民大都属羌、氐种;而疏勒以之北基本上为塞种、塞种人被大月氏逐出后一部南下建立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其余残部逃至疏勒西北建立休循,捐毒……等小国。而乌孙居民中,既有塞种又有大月氏种。在大沙漠以北的“北道诸国”,其居民多系原始的蒙古种。至于天山以北的诸国,既有原始的蒙古种,也有塞种人,也有羌族,其中大者如车师、乌孙。车师地肥美,有城廓田畜,乌孙地莽平,不田作,随畜逐水草,俗与匈奴同。西南夷地区的主要族群及其地理位置_作者段渝一、西南夷名称。有关西南夷较完整而详备的记载,首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此篇总叙部分记载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西南夷族类有异,成分复杂。按《史记》有关篇章所记,实际上包括西夷和南夷两部分。所说夷,即《西南夷列传》末句所记“蛮夷”,是汉代对巴蜀西南外少数民族的通称,西和南均为方位词,西夷是指巴蜀以西的少数民族,南夷是指巴蜀以南的少数民族。称巴蜀西南外少数民族为“西南夷”,是始见于西汉文献的称谓,在先秦文献并不如此。据《战国策?秦策一》所记载的张仪、司马错之言,蜀是“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这应当是秦国和东方六国的一致认识。《华阳国志?蜀志》也说秦灭蜀后,“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这里的“戎伯”指西南地区臣属于蜀的氐羌系和濮越系的各族君长。先秦时期臣属于蜀的族类众多,汶山、南中、僚、僰都曾先后为蜀附庸,蜀为其长,而称为“戎狄之长”,那么诸此族类也就是戎狄了。先秦文献中直接提到巴蜀西南外少数民族臣于蜀者,仅此一见,说明汉代所称西南夷,在先秦时代多称戎狄,这是随时代的变化所引起的称谓变化,这种名异实同,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常见的通例。应当指出,先秦史上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1],都是中原诸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称谓,是他称,非自称,是泛称,非专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或又合称为四夷[2],即四方之夷。关于这一点,唐孔颖达的解释最为精当。他说:“四夷之名,随方定称,则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其当处立名,则名从方号。”又说:“夷为四方总号[3]。”从《左传》、《国语》等先秦史籍可见,不仅“四夷”事实上都包有大量不同的族系,其中许多族系可以蛮、夷或戎、狄互称,而且这些名称亦多随时代的变迁而异同不一。无论先秦西南地区的戎狄,还是汉代的西南夷,都包括若干不同的族类,所说戎狄或西南夷,都是泛称,而不是一个统一或单一民族的族称。二、西南夷与南中。《史记?西南夷列传》总叙把西南夷分为四大类七个区域:第一类是夜郎、靡莫之属和滇、邛都,属于“魋结,耕田,有邑聚”族类的所在;第二类是巂、昆明,属于“编发,随畜移徙,无常处”族类的所在;第三类是徙、筰都、冉駹,属于“或土著,或移徙”族类的所在;第四类是白马,属于“氐类”的所在。很明显,这是以文化属性、民族系统和经济类型进行分类的。夜郎、靡莫和滇、邛都文化相近,均属濮越系族类,以定居农业为生产和生活方式。巂、昆明属于游牧的羌系族类。徙、筰都、冉駹属于氐羌系族类,其中有的是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有的则是半农半牧生产和生活方式。白马则属氐类[4]。除白马而外,在其他每一个类别中,均包括若干区域,每一个区域内都有“以什数”的众多“君长”,分别以一个“君长”代表一个族群,以区域中最大的记载代表区域。七个区域中有六个区域有“君长”,一个区域“毋君长”。如此看来,西南夷地区至少有上百个“君长”,所以太史公说“西南夷君长以百数”[5]。对于各个区域内“以什数”的“君长”,总叙只列出了当中最大的“君长”和主要“君长”的名称,他们分别是: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筰都、冉駹、白马,其中的滇属于靡莫之属,靡莫自然也是“以什数”的“君长”之一,而巂、昆明则是“毋君长”之属。所称“君长”,当然不是君主制时代的王或帝王,而是犹如“氐王、白虎夷王”一类族群的酋豪或首领,其性质如同鱼豢《魏略?西戎传》所记载的“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6],属于前国家社会的部落或酋邦之长。《史记?西南夷列传》总叙划分的七个区域,与汉武帝开西南夷所设置的犍为郡、牂柯郡、越巂郡、沈黎郡、汶山郡、益州郡等六个郡,具有历史、民族和文化等方面深刻的内在联系。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犍为郡包括西僰,属犍为南部;牂柯郡包括夜郎、且兰、同并、漏卧、句町等“故侯邑”;越巂郡包括邛都、筰都、昆明等部;沈黎郡原为筰都居地,汉武帝元鼎六年置郡,天汉四年罢置,筰都南迁至越巂郡之大莋、定莋、莋秦等地;汶山郡主要是冉駹居地,属于该地“七羌、六夷、九氐”的主要部分[7];益州郡主要是巂唐和昆明等居地。从汉至晋,西南夷郡县多有分合,其原由复杂,不过汉武帝开置此六个郡时,主要原因还是与族类和政治地理直接相关,《史记?西南夷列传》对于区域的划分亦当主要据此而来。《汉书?西南夷传》除将《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西南夷君长”改为“南夷君长”外,其他文字与之大同小异;《华阳国志》的记载则有所不同。《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移徙,莫能相雄长。很明显,《华阳国志》所记载的“南中”是一个地域范围的概念,而《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传》所记载的“西南夷”是地域与族群的概念,二者在概念上有所区别。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诸部均为“编发左衽,随畜移徙”,显系误记。按《史记》、《汉书》,滇、夜郎等均属“魋结、耕田、有邑聚”,只巂、昆明等为“编发、随畜移徙”。所以任乃强先生《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依《史记》文将此句增改为“或椎髻耕田,有邑聚,或编发、随畜移徙”[8]。第二,“南中”名称始见于三国蜀汉时期[9],《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南中诸郡并皆叛乱”,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说“亮至南中,所至战捷”,均可为证。南中,是用以指称蜀汉以南的地区,不属于行政建制和区划。蜀汉和晋代的南中并不是秦汉时期西南夷的全部,仅相当于秦汉时期南夷的大部分地区,而不包括秦汉时期的西夷。与《史记》和《汉书》相比较,《华阳国志》没有把徙、筰都、冉駹、白马等著录在《南中志》,而是把他们分别著录在《蜀志》和《汉中志》内。《华阳国志》之所以没有把《史记》、《汉书》的西夷以及部分南夷在《南中志》中叙录,这是因为晋时南中不包括秦汉的西夷以及南夷中的越巂等地区。《三国志?李恢传》裴松之注说:“臣松之讯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以总摄之。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晋时有“南中七郡”之说,即朱提、建宁、云南、兴古、牂柯、益州、永昌等七郡,自晋泰始六年置宁州以后,乃陆续分置为十四州。第三,《华阳国志》总叙将南中十四郡分为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等六个区域,其中滇濮是以族类名称(滇为族称,濮为族属)代表区域,叶榆和桐师是以地名代表区域,句町、夜郎和巂唐则分别是以族群和郡、县名称代表区域。显然,这是从区域即势力范围或地盘的角度立说,而不是从族群或郡县角度立说[10]。在常璩所划分的在六个区域内,“侯、王国以十数”,侯、王国即侯国和王国,这些以十数的侯国和王国即是《汉书?西南夷传》中屡次说到的“邑君”,邑君所谓“邑侯君长”,他们多数是从属于“最大”的君长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划分的六个区域,实质上就是六个大君长及其势力范围所在的区域。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西南夷传》及《华阳国志?南中志》可以看出,汉晋之间“西南夷数反”。汉昭帝元年“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汉成帝河平二年南夷夜郎王、句町王、漏卧侯等“更举兵相攻”,夜郎王兴“将数千人”,“从邑君数十人”见牂柯太守陈立,兴被断头后,“其妻父翁指与其子邪务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这表明,夜郎王、句町王均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都是称雄称长者。以此类推,南中各地均有最大君长的势力范围,他们于是成为南中“以十数”的侯、王国的典型代表。由于这样的缘故,南中地区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以势力范围为基础的政治地理区域,这就应当是《华阳国志?南中志》划分南中为六个区域的依据。三、西南夷地区的主要族群。以下按照《史记?西南夷列传》所叙顺序,综考七个区域内主要“君长”族类及其地域的基本情况[11]。1、夜郎。夜郎所在,历来歧说纷纭而莫衷一是。诸家或以为在今贵州桐梓,或以为在长顺,或以为在郎岱,或以为在罗甸,或以为在今云南曲靖,或以为在沾益,不一而足。清人多以《汉书?地理志》“犍为郡”下颜师古注引应劭之说,以为犍为“故夜郎国”,方国瑜先生从犍为郡治所的变迁考释夜郎地,同意《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引荀悦所说的“夜郎,犍为属国也”的看法,并认为夜郎当在贵州安顺府北部,抱有今安顺、普定、镇宁、关岭、清镇、平坝等县,其治所在沿北盘江之处[12]。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认为,“夜郎国”的疆界大致是:东起湄潭、遵义、贵阳、罗甸一线北到仁怀、叙永、高县一线,西至昭通、巧家、会泽、东川、曲靖一线,南抵兴义地区,大致以南盘江、红水河为界,此即广义的“夜郎国”疆域,而其中心区域则仅相当于汉夜郎一县之地,汉夜郎县的辖境则相当于今安顺地区及兴义地区的晴隆、普安和六盘水地区的盘县[13]。从史书看,其实夜郎的地理范围应是比较清楚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汉书?地理志》:“夜郎:豚水东至广郁。”《后汉书?西南夷传》注引《华阳国志》:“豚水通郁林。”《华阳国志?南中志》“夜郎县”载:“郡治,有遯水通郁林。有竹王三郎祠,甚有灵响也。”这几条材料可以说明两层意思。第一,夜郎国临牂柯江,豚水(豚水即遯水)通广郁、郁林。广郁为郁林郡下辖县,在今广西贵县东。据《水经注?温水》,豚水即牂柯江,水出夜郎,东北至谈稾县,又东迳且兰县,又东迳毋敛县西,又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此水的大致流向与北盘江及下游的红水河相合,亦合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可见遯水即是北盘江,而北盘江即是牂柯江[14]。第二,夜郎县应为故夜郎国的首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先君宗庙之主曰都,无曰邑。”东汉刘熙《释名?释州国》:“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汉代的夜郎县既“有竹王三郎祠,甚有灵响”即夜郎先祖的神祠,那么汉之夜郎县显然即是战国秦汉时期夜郎国的首邑之所在。学术界向有“大夜郎国”之说,其实所谓“大夜郎国”是以夜郎国为首脑或中心加上一些夜郎周边之小国形成的部落集团或酋邦集团,亦即以夜郎国为主体的夜郎酋邦社会,这就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载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所谓以什数的君长中的最大者,自然就是众多君长中的大君长,可以联合并动员其他君长形成一个松散的区域性政治集团。《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汉昭帝元年“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其中谈指为夜郎邑[15];同书又载汉成帝河平年间夜郎王兴带领数千人并有邑君数十人见牂柯太守,其妻父迫胁二十二邑反等,这些事例都说明了夜郎王拥有很大的势力范围,而其势力范围内的数十邑君并不属于也不等于夜郎国,而是夜郎国的附庸。《史记?西南夷列传》首叙夜郎,说夜郎在西南夷中最大,而不像其他君长仅在某一区域中最大,实际上已经表明了这个史实。夜郎属于古代的濮越系族群。《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说的牂柯,实际包括了夜郎,是夜郎的异称。夜郎在今贵州西南部与云南东南部。牂柯为百越民族语言,意为“系船杙”。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异物志》说:“有一山,在海内,似系船杙,俗人谓之越王牂柯。”可见,夜郎的主要居民是百越系统的民族。有的史籍称夜郎的主要居民为僚、濮,《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汉武帝通西南夷后,斩夜郎竹王,置牂柯郡,“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为立嗣”,这是说夜郎境内的夷人为濮族。但《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了同样事件,却将“夷濮”改称“夷僚”。这说明,僚、濮实为一族。《三国志?蜀书?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说:“牂柯、兴古,僚种复反”,《晋书?武帝纪》记其事为:“太康四年六月,牂柯僚二千余部落内属。”可知越、濮、僚是可以混称互用的,所指皆一,即今壮侗语族的先民百越民族。僚是古代南方一大民族,见于汉代史籍。南中一带,僚常与濮混称,而在岭南,僚又与俚混称并用。东晋时,僚人从今广西、贵州北上,“自汉中达于邛笮”。迄至宋代,广西部分僚人已改称壮,僚人的一部分为今日的仡佬族,可见僚人亦属濮越系的民族。2、靡莫、滇。滇为族名,同时也是国名,其中心在今云南滇池周围,对于这一点,学术界基本没有异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说,楚庄王苗裔庄蹻于战国时入滇为王,滇始与中原发生联系。从近年来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大量滇国遗物来看,滇文化的面貌已日益清晰。在此基础上,前人已对滇文化的族属作了有益的探讨[16]。我们以为,滇国的王室与主体民族应为濮人,亦即史籍所称的“滇濮”。滇与越为一大族系,二者同源异流,濮系民族为今日壮侗语族的先民[17]。靡莫,《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与滇“同姓相扶”,《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与滇“同姓相仗”,清楚地说明靡莫与滇同为濮越系族群。靡莫在滇国东北,从地理和考古资料分析,其地应在今云南曲靖。3、邛都。邛都,汉代又称之为邛都夷。《后汉书?邛都夷传》记载:“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汙泽,因名为邛池(今西昌邛海),南人以为邛河。后复反叛。元鼎六年,汉兵自越巂水伐之,以为越巂郡。”邛都夷是古代分布在安宁河流域的主要民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又载:“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又载:“南越破后……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白马为武都郡。”说明安宁河流域一带的古代民族是邛都夷。邛人的中心在今安宁河一带,以西昌为中心,其分布的最北面达到邛崃山以北的临邛县(今四川邛崃)。《华阳国志?蜀志》说:“临邛县,(蜀)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实之,有布濮水,从布濮来合。”又说:“阐县,故邛人邑,邛都接灵关,今省。”阐县在今四川越西县,晋代以前也有邛人居住。邛人分布的最南面是在晋代的会无县,即今四川会理县。《华阳国志?蜀志》说:“会无县,路通宁州,渡泸得堂狼县,故濮人邑也。”邛与濮为同族。可知邛人最北分布在邛崃山麓的临邛,最南分布在金沙江两岸的会无,亦有濮的称谓。最近几十年来在安宁河流域发现的大量大石墓,就是邛人的墓葬。汉代越巂郡,大体上就是先秦时代邛都夷的集中分布地区,主要包括今凉山州的西昌、德昌、米易、会理、会东、宁南、普格、冕宁、喜德、越西、甘洛、峨边等县、市,以今西昌市为中心。邛人属百濮民族系统。《史记?西南夷列传》将邛都与滇、夜郎划为同一族系,《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夜郎为“濮夷”,称滇为“滇濮”,可知与之同类的邛都也是濮系。《华阳国志?蜀志》“越巂郡”下载:“会无县(今会理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直接说明为濮人居地。所谓“濮人冢”,实即今天考古学上的大石墓。这种墓用大石砌墓室,顶部覆以大石,酷似石头房屋,当地彝族称为“濮苏乌乌”的住房。濮苏意为濮人,乌乌意为另一种民族。濮苏乌乌即濮人墓冢,此即文献所称的“濮人冢”[18]。大石墓的分布,集中在安宁河流域[19],即汉代越巂郡地。其年代上起商代,下迄西汉,其空间、时间都与邛都的活动相吻合,表明邛都确属百濮民族系统。4、巂、昆明。《史记》、《汉书》的《西南夷传》均称巂、昆明,《史记索隐》引崔浩曰:“巂、昆明,二国名。”《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永昌有巂唐县。”《续汉书?郡国志》“永昌郡”巂唐县刘昭注:“本西南夷,《史记》曰:古为巂、昆明。”《盐铁论?备胡篇》云:“氐僰、冉駹、巂唐、昆明之属”。可知巂即是巂唐,巂当为巂唐的省称,正如一些史籍把昆明省称为昆一样,如《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巂、昆明为“编发,随畜移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由此可知,巂、昆明同为氐羌系,属于藏缅语族的族群。巂、昆明故地甚为辽阔,“可数千里”。巂的地理位置,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认为,“今澜沧江、怒江两岸自保山县以北皆其故地,东接昆明、东北近越巂。”巂唐县所在,刘琳认为在今云龙县南境、保山县北境[20]。方国瑜先生则认为,巂唐县当在今保山平坝[21]。5、徙、筰都。徙,音斯,又作斯、斯榆、斯都。《史记?西南夷列传》:“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集解》引徐广曰:“徙在汉嘉。”此“汉嘉”指今四川雅安地区天全县。《华阳国志?蜀志》“越巂郡邛都县”下记有“又有四部斯臾”,斯即徙人。可见汉代居住在今四川凉山州西昌一带的徙人,原来是从天全迁徙而来的。徙人是羌族的一支。《续汉书?郡国志》“蜀郡属国”下载:“汉嘉,故青衣。”《水经?青衣水注》载:“(青衣)县,故青衣羌国也。”《华阳国志?蜀志》说汉初吕后时“开青衣”,即包括徙在内。同书又说武帝天汉四年于故沈黎郡置两部都尉,“一治牦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汉民”,徙属外羌之列,应为牦牛种青衣羌,所以青衣江又称为羌江。筰都,筰(《史记》)或作莋(《汉书、《后汉书》》)、笮(《华阳国志》)。《后汉书?莋都夷传》记载:“莋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沈黎郡所在,《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均未载。《华阳国志?蜀志》说:“元鼎六年……西部笮(都)为沈黎郡……天汉四年,罢沈黎,置两部都尉,一治牦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汉民。”《后汉书?莋都夷传》亦载:“至天汉四年,(沈黎郡)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安帝延光二年改为蜀郡属国,灵帝时改为汉嘉郡。可见,此汉嘉郡辖境大致上就是沈黎郡辖境,基本无变迁。其境地域范围,据《续汉书?郡国志》载,汉嘉郡(今雅安地区)辖有汉嘉(今四川芦山县)、严道(今四川荥经县)、徙(今四川天全县)、旄牛(今四川汉源清溪镇)四县。汉嘉为青衣羌国;严道,据考古发掘,春秋时为蜀人所居,战国时则形成蜀人、秦人及楚人错居之局,文献记载则有邛人,总之均与羌无关;徙即徙都。此三县均无筰都立足之处。因此,只有牦牛一地为筰都所居。由此可见,秦汉以前筰都分布在今四川汉源。据《华阳国志?蜀志》,汉武帝元鼎六年所置沈黎、汶山、越巂、武都四郡,“合置二十余县”。《汉书?地理志》所载此地域范围内的县数,除去因郡境变化归属不同从而重复的县,以及后来设置的县数,共二十余县,基本上与《华阳国志》合。根据史籍的记述来看,战国以至汉初,筰都仅分布在今汉源大渡河南北,汉武帝末叶以后才逐渐南迁至雅砻江今凉山州西南地区。近年在四川凉山州盐源县所发掘的西汉时期的青铜文化墓葬,当是筰都的文化遗存[22]。筰都的北界,据《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华阳国志》:“邛崃山本名邛莋(山),故邛人、莋人界也。”此邛崃山即是今大相岭,其东北为邛,其西南为莋。可见,筰都北界不能逾越大相岭。 筰都以南,本为邛都分布之地,汉初以前筰都南界当不过今凉山州之越西。《汉书?地理志》“越巂郡”属县中之定莋(今盐源县)、莋秦(今盐源县境)、大莋(今盐边县)等三莋,应是汉武帝以后筰都南迁所居之地[23]。筰居汉源,在先秦时已如此。《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汉兴而罢。”既然秦代已在筰都设县,则筰都的始见年代必在先秦时代。又,“邛、筰、冉、駹者近蜀”,是由南而北记述,说明筰在邛之北,这正是先秦、秦代以至汉武帝时的格局。筰都南迁的年代,当在汉武帝天汉四年前。《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以“西部笮为沈黎郡”,即以筰都为沈黎郡郡治。但自天汉四年沈黎郡并蜀为西部都尉,而两都尉分驻牦牛和青衣后,筰都县即不再见于记载。《汉书?地理志》记载东汉和帝以前,蜀郡已无筰都县。至安帝延光二年改蜀郡西部都尉为蜀郡属国,辖四县,也无筰名。可见,在武帝天汉四年,筰随同罢置。其原因,完全可能与筰都南迁有关。筰都是牦牛羌的一支,当是牦牛种之白狗羌。《后汉书?莋都夷传》说:“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即与岷江上游的“阿巴白构”有关,而阿巴白构正是白狗羌。《史记?大宛列传》正义说:“筰,白狗羌也。”确切说明筰都是白狗羌,应是岷江上游白狗羌南下的一支。6、冉、駹。冉、駹分布在岷江上游,是冉和駹两个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合称。《后汉书?冉駹夷传》记载:“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冉、駹的中心位置,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一带。冉、駹原为两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因朝冉从駹,定筰存邛”,《史记?大宛列传》:“乃令张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均分而言之。冉、駹得名,与冉山和駹水有关[24]。冉得名于冉山,唐于茂州都督府下设有冉州冉山县,可知冉山在茂。駹得名于駹水,《续汉书?郡国志》“蜀郡汶江道”刘昭注引《华阳国志》说:“濊水,駹水出焉,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孝安延光三年复立之以为郡。”汉汶江道在今四川茂县治北,可知駹水亦在茂。《华阳国志》又于绵篪道说:“有玉垒山,出璧玉,湔水所出。”这样看来,湔水是当地的主流,即今岷江上游,駹水则是湔水的支流,可能就是杂谷脑河。由此亦可看出,冉、駹是两个并存的部落,所以才被史籍予以并称。《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使。乃以邛都为越巂,冉、駹为汶山郡,广汉白马为武都郡。”《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云:“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可见汶山郡是因汉破南越、灭邛、筰及且兰后,冉、駹振恐请臣而设置的。冉、駹这种归附,是“纳土归附”,设治当在原有部落的中心,以利于统率经营,所以汶山郡的中心亦当是原冉、駹部落的中心。汶山郡的区域主要在今岷江上游的茂县一带,其郡治在今茂县凤仪,则凤仪一带就不仅是冉、駹的旧地,而且还是这些部落的中心。所以,《史记?六国年表》正义说:“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旧唐书?地理志》于茂州说:“汶山,汉汶江县,属蜀郡,故城在今县北二里,旧冉、駹地……贞观八年改为茂州。”冉、駹故地在岷江上游今茂县一带,应该说是十分清楚的。冉、駹都是氐族。《后汉书?冉駹夷传》记载:“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数十丈,为邛笼。”邛笼即《先蜀记》所载蚕丛氏所居的石室。《魏略?西戎传》记载氐族中有“蚺氐”,又说“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故字从虫。说明冉、駹为氐族。汉初所设湔氐道,在今汶川一带,“氐之所居,故曰氐道”[25]。这些都是冉、駹为氐族的确切证据。 《后汉书?冉駹夷传》记载冉、駹“其王侯颇知文书”,《魏略?西戎传》说氐人“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南史?武兴国传》也载氐人“知书疏”,而《北史?宕昌羌传》和《党项传》则均言羌“无文字”。由此亦知冉、駹并为氐族。7、白马。《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白马即指白马氐,先秦时分布在今四川绵阳地区北部与甘肃南部武都之间的白龙江流域[26]。至汉代,上述白马氐之地多见羌人活动,称为“白马羌”,表明羌族中的一支已迁入其地,而因白马之号[27]。这支羌人,即《后汉书?西羌传》所说“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的白马羌。白马羌的分布,除今绵阳地区北部外,也向西延展到松潘。也有学者认为武都的白马羌实为参狼种,只有蜀郡西北的才是白马羌[28]。除了《史记?西南夷列传》的总叙部分而外,在该篇的具体叙述中以及在《汉书?西南夷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和《华阳国志》等文献的记载中,还可以见到西南夷其他一些族群或类似于“君长”的“邑君”及其名称,主要有: 1、僰。先秦时期,僰人集中分布在四川宜宾至云南昭通一带。《华阳国志?蜀志》“犍为郡”下记载:“僰道县,在南安(今四川乐山市)东四百里,距郡百里,高后六年城之。治马湖江会,水通越巂。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汉书?地理志》“僰道”下应劭注曰:“故僰侯国也。”可知今四川宜宾一带是僰人的分布中心。僰人很早就在川南地区定居,成为川南的主要民族。《吕氏春秋?恃君览》:“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多无君。”《礼记?王制》:“屏之远方,西方曰棘。”棘即僰。郑玄注云:“棘,当为僰(“为”字据惠栋校宋本增)。僰之言偪,使之偪寄于夷戎。”僰人入居川南的年代,可追溯到殷末以前,殷末杜宇就是来自朱提(今云南昭通)的僰人。而朱提汉属犍为郡之南部,蜀汉始分置朱提郡。《说文?人部》:“僰,犍为蛮夷也,从人棘声”,说明朱提古为僰人居地,与今宜宾地相连接。方国瑜也认为僰人以僰道县为中心,散居其南境,《秦纪》所言的僰僮应在犍为南的朱提之地[29]。杜宇既为朱提僰人,殷末即已北上至蜀,说明殷末以前僰人已是定居在汉之犍为郡即今川南至滇东北地区的民族。僰人是濮之支系,僰即濮。以声类求之,“僰,蒲北反”[30],蒲、濮双声叠韵,故得相通。《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的“滇僰”,《华阳国志?南中志》作“滇濮”,证实僰为濮系民族。因其居于棘围之中,故称僰人,“从人棘声”[31]。所谓僰人,即是居于棘围之中的濮人[32]。僰人又常被华人称为“西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唐蒙略通夜郎、西僰”,“且夫邛、筰、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皆是。所言西僰,均应导源于上引《吕氏春秋?恃君览》和《礼记?王制》,都是指犍为之僰。“西”为方位词,因僰在华夏之西,故名。但由此却引起了僰人族属的争议。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及《淮南衡山列传》、《后汉书?杜笃传》、《文选?长扬赋》等,每以“羌、僰”并述,《后汉书?种暠传》又说僰为“岷山杂落”之一,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徐广曰;“僰,羌之别种也。”固然秦以后僰人之一部有可能因“汉民斥徙之”,北迁至岷山山谷,但至少从先秦到西汉初叶人们都还能明辨僰、羌有别,是不同的族类。《淮南子?齐俗篇》:“羌、氐、僰、翟,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鞮,不能通其言,教俗殊故也。”象,狄鞮,皆汉语“翻译”之义[33]。虽屡经辗转翻译,羌、僰之间仍不能通其语言,足见两者语言差异很大。而“教俗殊故也”一语,更确切指明了两者文化和风俗都完全不同,可见僰人非羌。2、且兰。《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武帝元鼎六年因犍为发南夷兵击南越,“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及至汉军破南越,以平南越之师还诛且兰君,“遂平南夷为牂柯郡”。为汉军所平的且兰,《史记?西南夷列传》记为“头兰”,《汉书?西南夷传》记为“且兰”,《水经注?江水》则采折衷之说曰:“且兰,一名头兰。”实际上,头兰应是且兰。《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南越既平,汉军“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索隐》注头兰曰:“即且兰也。”《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此事,除诛且兰外其余与《史记》大同:“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柯郡。”颜师古注说:“谓军还而诛且兰。”《史记》、《汉书》并说汉军还而行诛头兰或且兰君,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即以头兰或且兰为牂柯郡郡治。《汉书?地理志上》记载牂柯郡郡治为“故且兰”,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且兰侯邑也。”《华阳国志?南中志》且兰县下记载:“汉曰故且兰。”《续汉书?郡国志五》亦载牂柯郡郡治为“故且兰”。到三国时,《水经?江水》记载该县名为“且兰”,已省“故”字。《水经》作者为三国时人,可知很有可能且兰县省故字,时间是在东汉末叶。此后直到两晋,该县仍称且兰〔34〕。可见,既然牂柯郡郡治为故且兰县,而故且兰县是武帝时平南越的汉军还诛且兰君后设置,此后一直沿用且兰县名,那么《史记》所说的“头兰”自然也就是《汉书》和《后汉书》所记载的且兰。从历代该县县名的沿袭可知,应以作且兰为是。且兰的所在,据诸家考证,当在今贵州黄平至贵阳一带[35]。且兰的族属,当与夜郎相同,为濮越系族群。《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裴松之注引《益部耆旧传》说:“牂柯、兴古,僚种复反”,《晋书?武帝纪》记载此事为:“太康四年六月,牂柯僚二千余部落内属。”可知且兰为僚,而僚、越、濮所指皆一,在《华阳国志?南中志》又称为“夷濮”,实即今壮侗语族的先民百越民族。关于这一点,已在前文关于夜郎族属的讨论中指出,可以参看。 3、劳浸。《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司马贞《索隐》说:“劳浸、靡莫,二国与滇王同姓。”《汉书?西南夷传》:“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劳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听。”劳浸与劳深,“浸、深”二字当属形近而讹,应以作“劳浸”为是。方国瑜先生推测劳浸为地名,靡莫为族名,并认为司马贞以为劳浸、靡莫为二国,其说未必可从[36]。但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看,劳浸与靡莫和滇既然是“同姓相扶”,那么劳浸必然是这个“同姓”族群中的一支,并非地名。《史记?西南夷列传》还记载:“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十分清楚地说明劳浸与靡莫一样是西南夷诸族群中的一支,而非地名。况且,在西南夷地区后来的郡县地名中,并没有劳浸名称,可见劳浸决不会是地名。4、句町。句町,《汉书?西南夷传》作鉤町。《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汉武帝元鼎六年置牂牁郡,漏卧、句町,并属牂牁郡。方国瑜先生考证句町地在盘龙江上游,童恩正先生认为广西的西林也是句町地,刘琳先生认为句町故城在今云南广南,云南之富宁,广西的西林、隆林、田林等县亦当为句町辖境[37]。王先谦《汉书补注?西南夷传》曰:“句町,牂柯县,在临安府通海县东北五里。”通海南临礼社江(元江)不远,礼社江即《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僕(濮)水”。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中考证“此水(指濮水)自叶榆地区流至西随,又至交趾入海,则为今之礼社江,下游称红河之水,即《汉志》之濮水”[38]。濮水因沿岸多濮人而得名。句町的势力范围较为广大,《汉书?西南夷传》:汉昭帝五年,因“鉤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亡波为鉤町王。”亡波为侯,既可率其所属之邑的君长和人民斩首捕虏,可知句町的范围较广,所属邑及邑君长亦复不少。正因句町实力较强,所以才敢于在汉成帝河平年间与夜郎王、漏卧侯“更举兵相攻”[39]。根据沿濮水一线出土的的文物面貌基本相同的特点分析,沿濮水(礼社江、红河)的元江、红河、个旧一线,大概也是句町的势力范围和句町文化的影响区域。句町为濮系民族,《华阳国志?南中志》明确记载:句町县“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至今”。5、漏卧。《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并载有漏卧县,置自西汉,东汉、蜀汉因,晋省并。《汉书?地理志》“漏卧县”颜师古引应劭曰:“故漏卧侯国”,可知漏卧原为部落或酋邦。漏卧与夜郎、句町相邻,汉成帝时曾相互举兵攻战,《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考证:“因其(漏卧)地在句町以北,夜郎之南”,刘琳先生考证漏卧在云南宗师一带[40]。漏卧属于濮越系族群。《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兴古郡“多鸠僚、濮”,蜀汉时漏卧县属兴古郡,故知漏卧为濮,当无疑义。 6、滇越。《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然闻其西(按,此指昆明之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滇越的地理位置,丁山以为是位于汉代的哀牢地区,在今云南保山市的腾冲,方国瑜先生对此说曾详加论证[41]。汶江先生认为,滇越之地应是在今东印度的阿萨姆邦[42],童恩正先生亦同意此说[43]。从地理方位、中印交通等角度看,汶江先生的看法应当是可信的,把滇越的位置定在阿萨姆实比定在腾冲更加合理[44]。7、哀牢。《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哀牢)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后汉书?哀牢传》记载:“(哀牢夷)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方国瑜先生认为,据此可见,哀牢地广人众,包有今之保山、德宏地区,及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带[45]。方先生之说,符合古文献的记载。 此外,见于史籍记载的西南夷其他族群,还有“廉头、姑缯、封离”等,但都是语焉不详,文略不具,这里不再讨论。论汉代“西南夷”区域内的人群类别称谓--西陆网从现有文献记载看,最早涉及藏彝走廊地区部落人群活动的史籍可能是《尚书·牧誓》,云:“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孔氏传曰:“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孔颖达疏曰:“此八国,皆西南夷也”。《牧誓》“八国”既然包括了位于江汉之南的“庸、濮”在内,故唐人孔颖达所言“西南夷”不同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巴蜀西南外蛮夷”,但位于以华夏为中心的西南方位当可肯定。据《后汉书》、《华阳国志》记载,“羌、濮”两类人群早在先秦时期即已有部分支系活动于藏彝走廊中[1]。至于“卢、髳”二部,有学者认为其与彝族、纳西族的先民有密切关联[2]。由于史料记载简略,我们尚不能确定《尚书》所记“羌、濮、卢、髳”等部的活动范围是否已与藏彝走廊某些区域相重合,但他们与汉代“西南夷”有某种渊源的可能性显然不可排除。《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於南夷’。”邛、筰、冉駹皆在今天藏彝走廊东缘一带。“秦时尝通为郡县”说明秦人曾直接与走廊边缘地带的人群发生了接触,但史籍中并无相关秦朝对于走廊部落人群认识的记载。一般认为,《史记·西南夷列传》是目前所见最早比较明确记叙汉初西南地区部落人群分布及活动情形的汉文史籍,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在以上这段记载中,所举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筰都、冉駹、白马等都是部落人群名称,与其相关的人群类别称谓主要有两个:一是“西南夷”;一是“氐类”。《史记》既然以《西南夷列传》为名,且所叙“君长以什数”中较大的部落都归入“西南夷”这个概念下,说明以上部落均应属“西南夷”范畴。从“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一语判断,“西南夷”的方位当以巴、蜀而非长安作为参照系[3],这表明以上部落均分别在巴、蜀的西南方位。“西南夷”一称中的“西南”二字既然是作为方位词出现,可知《史记》中对于汉代巴蜀西南外各部落人群均以“夷”统称之。除“西南夷”外,《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还出现了“氐类”一称。一般认为,“皆氐类也”一语是指白马诸部,并不包括前举之邛都、徙、筰都、冉駹等部落[4]。“氐”见于文献记载的时间相当早。《诗经·商颂》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荀子·大略篇》记:“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吕氏春秋·恃君篇》亦记:“氐羌、呼唐,离水之西”。《荀子》、《山海经》、《吕氏春秋》都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5],故有人认为“氐”至迟在战国末年已为中原人士所知晓[6]。“氐”又常与“羌”并用,有学者认为“氐”是从羌人中分化出来的一支,或以为“氐”系为“低地之羌”[7]。由此可见,“氐”在秦汉以前的文献中即已经作为一个人群类别称谓存在了。依此背景,汉代史家司马迁应当对“氐”的族群内涵有一定了解,他将“自冉駹以东北”说成“皆氐类也”当有其依据。因此,据司马迁的描述,汉之“西南夷”中又大致可分作“氐”与“非氐”两类。石硕先生对此指出,在以上九个部落中,“司马迁明确给出具体族属的唯有“皆氐类”的白马,而对其余八个部落则均未给出具体族属。”[8]《史记》中对于巴蜀西南外各部落人群均以“夷”统称之,但由于“夷”这个人群称谓同时又将“氐类”人群包括在内,说明“西南夷”之“夷”在《史记》中显然是作为一个大的人群泛称之含义,还不能作为有严格人群区分意义的类别称谓。司马迁虽然用“夷”来泛称巴蜀西南外各部落,但在具体涉及到某些部落时却又别之曰“西夷、南夷”[9]。《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亦云:“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可见《史记》中可被明确归入“西夷”的有邛、筰、冉駹、斯榆四个部落。邛、筰乃是“邛都、筰都”的省称,而《司马相如传》中的“斯榆”当指《西南夷列传》中的“徙”而言。《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曰:“徙音斯”,《史记·大宛列传·索隐》李奇云:“徙音斯”。《汉书》卷61《张骞传》、卷86《西南夷传》颜师古注均有此说。以上各注表明,“徙”在作为人群称谓时与“斯”同音。至于斯榆之“榆”,任乃强先生认为是古藏缅语“地区”之意[10],故“斯榆”可理解为“斯之区域”。这说明“斯榆”在作为人群称谓时最重要的乃是“斯”,这与用“徙”表达并无区别。“南夷”是一个与“西夷”相对应的概念。“南夷”在《西南夷列传》中被多次提到,如: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后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11]。根据这些记载,《史记》中明确归入“南夷”这个概念之下的只有“夜郎、且兰、头兰”三个部落[12]。通过以上梳理,可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开篇所举九部落中被称作“西夷”的有邛都、徙、筰都、冉駹四个部落,被明确置入“南夷”之下的只有夜郎。至于滇、巂、昆明、白马四个部落,《史记》中并未明确指出它们究竟是属“西夷”,还是“南夷”。这就是说,《史记》中虽用“西南夷”统称巴蜀西南外的九个主要部落,但在具体使用“西夷、南夷”两个概念时却有着较为严格的区分。邛都、徙、筰都、冉駹被称作“西夷”是由于这四个部落位于巴、蜀之西,夜郎属于“南夷”同样是由于该部落位于巴、蜀之南。我们注意到,以上五个部落与汉地之间没有间隔任何部落,这可能是它们可以被具体指称的关键因素。滇、巂、昆明三个部落在方位上处在“西夷”与“南夷”之间[13],且与汉地并不直接相邻(汉、滇之间隔着夜郎与头兰,而巂、昆明位于滇之西)。这极可能是《史记》未将这三个部落归入“西夷”或“南夷”的重要原因。但“皆氐类”的白马无疑已与汉地相接,却并未被包括在“西夷”或“南夷”之下,说明“夷”在《西南夷列传》中当被具体使用时并不包括“氐类”人群[14]。值得注意的是,在成书于东汉后但却主要反映汉代巴蜀西南外区域部落人群面貌的《华阳国志》与《后汉书》两部史籍中,有关“西南夷”人群类别的认识与《史记》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史记》在记叙“西南夷”各部落时均直呼其名。《汉书》也是如此。但《后汉书》在记叙“西南夷”各部落时除对夜郎、滇、巂三个部落直呼其名外,对其余五个部落则分别在其名称后缀上“夷、氐”两种相对固定的人群称谓[15]。如记“邛都”作“邛都夷、莋都”作莋都夷[16],“冉駹”作冉駹夷,“昆明”作昆明夷,“白马”作白马氐。也就是说,《后汉书》中除明确将白马归作“氐”,还明确将邛都、莋都、冉駹、昆明四个部落归入“夷”之类别。这一现象表明,“夷”在《后汉书》中已经不是一个人群泛称,而是一个与“氐”不同的具体人群类别。东汉时期“夷”开始作为人群类别出现尚有以下两条重要证据:其一,《华阳国志·蜀志》记:“筰,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佩文韵府》曰:“种,类也。”可知所谓“夷种”就是指属于“夷”之类别的部落人群。“汶山曰夷”指居于汶山郡的“冉駹夷”而言,“南中曰昆明”指“昆明夷”。“汉嘉、越嶲曰笮”,以意解之,自然指汉嘉、越巂二郡的“莋都夷”。《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灵帝时,以蜀郡属国为汉嘉郡。”《后汉书·郡国五》“蜀郡属国条”云:“汉嘉故青衣,阳嘉二年改”,其领徙、旄牛、严道等县。据此可知,东汉阳嘉二年(年)曾以青衣县为基础设立汉嘉郡,由其所领县域看,正包含了原沈黎郡所在的“莋都夷”地区。另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五》及《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越巂郡领有“莋秦、定筰、大筰”三县。此三县既然以“筰(莋)”命名,显然是由于其地主要为筰(莋)人的分布区域。“越嶲曰笮”应即指此。至于“蜀曰邛”,由于两汉时期“邛(即邛都夷)”主要分布在越巂郡而非蜀郡,“蜀”在句中极有可能是指古蜀国而言。因此,这句话可理解为“古代蜀国有被称作‘邛’的人群”。由此可见,《华阳国志》明确将《后汉书》中被称作“某某夷”的部落人群归入“夷”这一人群类别中。其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此记载说明:第一,“夷”是一个与“氐、羌”相并列的人群类别称谓;第二,东汉汶山郡一带不仅有“夷”,且分布着氐与羌。《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中尚未出现汶山郡一带有“氐、羌”的记载,但《后汉书》中不仅明确称“冉駹”作“冉駹夷”,而且还肯定的指出该地区“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只有当中原人士对分布于汶山郡各地的部落人群有相当了解并有所比较的基础上才能够形成“夷、氐、羌”三类人群“各有部落”的认识,表明在《后汉书》语境中“夷”已明确作为一个不同于“氐、羌”的人群类别称谓。滇、夜郎、巂[17]在《史记》中被归入“非氐”一类,但无论《史记》还是《后汉书》在记载这三个部落时都直呼其名,那么他们究竟属于什么人群类别呢?《华阳国志·南中志》对此有一条重要记载,曰:“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此记载说明南中地区昔日存在着“夷、越”两种人群类别。据任乃强先生考证,《华阳国志》成书于东晋后期[18],但由“在昔”一语可知南中为“夷、越之地”的认识应产生于东晋以前。同时《蜀志》谈到古蜀疆域时称:“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石硕先生认为:“按照此语境,当蜀‘北与秦分’之时‘南接于越’。这表明蜀之南即南中地域有‘越’的认识,至少应产生于蜀‘北与秦分’之时,即应产生于秦或秦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19]。根据石硕先生的分析,南中有“越”的认识早在先秦(包括秦)时期即已产生。因此,在常璩生活的时代之前,南中地区被认为主要由“夷、越”两种类别人群组成。至于南中地区的“夷”类人群,《华阳国志》中有两则记载:一是前引《蜀志》中有“南中曰昆明,……皆夷种也”一语;一是《华阳国志·南中志》记:“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昆”即“昆明”,其称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一直存在。可知南中地区汉代属于“夷”这一人群类别主要有“昆明”和“叟”。因此,当时与“昆明”和“叟”同时并存的应当还有属于“越”之类别的部落人群。滇、夜郎不被称作“某某夷”或被归入“夷种”,说明这两个部落人群应属于南中地区的“越”之类别。以上通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史籍中相关汉代“西南夷”各部落所属人群类别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初步认识:《史记》、《汉书》中开始用“西南夷”来泛称巴蜀西南外的各个部落,其中只有白马被明确归入“氐类”,至于其余部落具体所属人群类别不明。《后汉书》中已开始将“夷、氐”两种称谓相对固定的加在某些部落名称之后,其中被称作“某某夷”的部落在《华阳国志》中又被明确归入“夷种”加以认识。这表明“夷”在后两部史籍中已作为一个与“氐”不同,且有具体所指的人群类别称谓,而不再被用来泛称所有的巴蜀西南外部落。根据“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及“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等记载,汉代岷江上游以及南中等地与“夷、氐”同时存在的人群类别还有“羌”与“越”。由于“巴蜀西南外”区域主要属于藏彝走廊的范围,据以上史籍记载汉代走廊中主要存在“夷、氐、羌、越”四种人群类别。那么,汉代藏彝走廊中属于每个人群类别之下的部落分别有哪些?这四个人群类别在藏彝走廊中又具体呈现出怎样的分布格局?本文将在以下各节分别予以讨论。注释:[1]如《后汉书·西羌传》记秦献公时羌人附落南下进入到了藏彝走廊地区。《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蜀早期疆域“南接于越”,表明藏彝走廊南端在先秦时期可能就是属于“越”之系统的“濮”类人群活动。[2]如清代学者王崧在《道光云南志钞》中指出:“周武王牧野之誓有卢人,滇之倮即卢之转音。”此后,庄学本《西康夷族调查报告》中也赞成这一看法。石硕先生在《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一书中曾指出:“《尚书》和《诗经》中作为西方之部落族名称的‘髳、髦’,显然与后来《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所记的‘髦、旄、牦’等部落称谓系同一所指”(请参见石硕:《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四川人民社年版,第页)。方国瑜先生在《么些民族考》中指出:“旄牛以旄族得名,字或作犛、氂、髦、猫,并与摩字同音,而摩沙之‘沙’,在其族语中意为‘人’或‘族’。”可见“么些”之“么”可能源于“髳”(方国瑜《么些民族考》,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4期,年;此处转自李绍明: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四川大学社年版,第页)。[3]童恩正先生认为:“司马迁是以巴蜀为中心,叙述了其南方的贵州西部、西南方的云南滇池区域、洱海区域、四川西昌地区、凉山彝族自治州以及北部的甘南武都地区的少数民族,而概括的称之为‘西南夷’”(《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年版,第93页)。林超民、秦树才在《秦汉西南夷新论》一文中也提出:“以往不少学者认为‘西南夷’是指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其实,‘西南夷’的‘西南’不是中国的西南,而是巴蜀的西南”(《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社年版)。另请参见祈庆富:《南夷、西夷考辨》,载《云南社会科学》1年第5期。[4]顾颉刚说:“其(指《史记·西南夷列传》)结语云:‘皆氐类也。’则不知其综西南夷言之乎?抑但综冉駹东北之白马诸国言之乎?清陈奂作《诗毛氏传疏》,……,主后一说。从陈奂言,凡西南夷均作氐,氐之区域至广远。”说明顾颉刚赞同将所有的西南夷部族均视作“氐”(顾颉刚《史林杂识》,中华年版,此处转自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四川大学社年版,第97~98页)。马长寿先生在《氐与羌》一书中对这种观点提出否定意见,指出:“原文徙、莋都二族与冉駹并列,谓‘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已作一小结。下文‘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谓‘皆氐类也’,又作一小结。最后一语‘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是总结上文及前未引文中的夜郎、滇、邛都、嶲、昆明之类皆为西南夷。‘自冉駹以东北’,‘白马最大’,则白马氐之类不能包括冉駹,正如冉駹之类不能包括莋,徙、莋都之类不能包括嶲、昆明一样,所以冉駹应当是在氐类之外的。冉駹如此,他如徙、莋都之不能称为氐类更可知”(马长寿《氐与羌》,广师大出版社年版,第20~21页)。马先生所论甚是,今学界一般认为“氐”仅指白马而言。[5]荀子(约公元前~前年),名况,战国后期赵国人,法家代表人物(请参见章诗同:《荀子简注》,上海人民社年版)。《吕氏春秋》乃战国时期秦相吕不韦组织宾客所撰。至于《山海经》成书时间的考证,请参见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与产生地域》,载《中华文史论丛》年第1期。[6]请参见杨铭《氐族史》,吉林教育出版社年版,第17页。[7]请参见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年版,第51页。[8]请参见石硕《汉代西南夷之“夷”的语境及变化》,载《贵州民族研究》年第1期。[9]童恩正先生说:“司马迁虽然将篇名称为《西南夷列传》,但实际上又将这些民族分成‘南夷’和‘西夷’两部分。由于澄清这一问题,对于研究西南少数民族颇为重要,所以我们首先加以讨论。”这说明童恩正先生认为《西南夷列传》中的“西夷、南夷”乃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请参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年版,第92页。[10]任乃强先生指出:“‘榆’字,羌、氐语族落地区之义”(《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社年版,第页)。此“羌、氐语族落”应指古藏缅语民族。格勒先生亦认为:“‘榆’为藏语,是国土或地方之意”(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四川民族出版社年版,第72页)。直至今天,藏区还有“察隅、珞瑜”,其中“隅、瑜”都是地区之意。[11]引文中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非原文所有。[12]唐司马贞《索隐》称头兰“即且兰也”,但未给出具体依据。[13]《史记·西南夷列传》记:“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唐张守节《正义》曰:“在蜀南以下及西也”,可知唐人也不确定“滇”到底是位于西还是南,巂、昆明显然也是如此。[14]石硕先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史记》语境中的‘夷’尽管不是一个确定的人群族属类别称谓,但‘夷’之所指显然已同‘氐类’有别。”请参见石硕《汉代西南夷之“夷”的语境及变化》,载《贵州民族研究》年第1期。[15]“徙”作为“西南夷”九部落之一不见于《后汉书》记载。[16]《史记》“筰都”,在《汉书》《后汉书》中作“莋都”,《华阳国志》中写作“笮、筰”,实皆同字异写。[17]《华阳国志》中并无相关“巂”部落记叙,但出现了与“巂”有关的“巂唐”一称。目前学界对于“巂”之族属面貌意见颇不一致,或认为“巂”为塞种人(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社,年,第36~44页),或认为“巂”即叟(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社年版,第27~28页),或认为“巂”为南迁蜀人的后裔(徐中舒《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载《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中华年版,第页)。笔者倾向性认为“巂”与“叟”有密切关联:一是《史记》中将“巂”与“昆明”并举,而《华阳国志》中却将“昆明”与“叟”并举;二是这两个人群称谓的发音相近。但“巂”与“叟”之间目前还存在着许多缺环,尚需学界的进一步探讨。[18]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部分,上海古籍社年版。[19]参见石硕《汉晋时期南中的“夷、越”辨析》,载《民族研究》年第1期。赞赏 长按白癜风感恩回馈北京治白癜风哪家好
|
时间:2018/1/9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
- 下一篇文章: 你相信世界上有奇迹吗她坚信有爱就有奇迹